算起来,已经是金融危机第五个年头了——背负巨大压力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员,今年终于过了一个平静的夏季假期。本来大家休假回来还想继续拿“欧债危机”说事儿,可惜美联储偏偏推出个充满“悬念”的QE3,一时间抢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版,欧元汇率也硬挺挺地重回1.30一线。九月中旬,国际资本价格再次亢奋起来,不久前还在为欧洲未来担忧的看空者,一夜之间都倒向了多头!
正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对QE3的批评,这些随风倒的金融投机客,关心的只是市场对“又一颗QE糖果”的热度,而经济体本身的承受力,才是决定QE3对资产价格作用的根本。当然,也有力挺QE3的经济学家,例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他把美联储的举动称赞为“明智之举”,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超级通胀担忧是多余的”(2012-09-21)。
对于沃尔夫先生的结论,我在一定意义上是同意的,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居民消费价格”联动并不具备必然性。货币政策影响更多的是资产价格,或者叫资本价格,说到底是一个“国家间财富分配”的问题。因此,各国利用货币政策引导资本流入本国实体经济,才是货币博弈的真实目的。因此,美联储不拘一格地推出QE1和QE2,在现代货币银行学的范畴,是合理的(效果好坏尚需时间的检验)。但是,新近推出的QE3显然是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
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于实体经济中信用杠杆的局限性,说白了就是资产泡沫早晚有破灭的一天!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效果就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经济参与个体,对自身信用杠杆的延展。统计美国从1970年代到今天的经济总体债务杠杆,即“居民+企业+政府”总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会发现美国经济的债务比率(Total debt ratio)已经从约100%增加到240%左右。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进程,一定程度上被连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延缓了。
当然,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过去四十年间,欧元区和英国的总债务比率也翻了一番,日本更是从170%增长到接近400%,直接导致了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日本经济发展遇到的流动性陷阱!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国家的债务杠杆到底多少为合理?除了通货膨胀,什么因素才是决定债务比例的关键?像中国这样一个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国家,需不需要通过货币杠杆撬动本国消费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债务比率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发达经济体债务扩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全球化经济大背景下,全球资产货币化的进程使得经济体对信用杠杆的容纳得到了深化。具体讲,一个企业的目标市场从四十年前的一国或者地区,已经扩展到全球,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使得信用融资背景下的投资扩张变得更加经济。例如,一个小小的新产品iphone5的订单可以瞬间达到200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国家也是一样,我一向不赞成把国家间货币政策博弈称为“货币战争”,因为战争意味着毁灭和灾难!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债务杠杆的扩张得到了货币政策的支撑,支撑了物质生产和全球流通。如果没有各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人类不可能享受如此富足的生活。世界的财富增加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货币不战争!
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通过货币政策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在财富分配上取得战术性的效果。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通过对有效汇率的干预,贬值本国货币促进本国出口。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意图,则是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压低美国政府、企业、个人的融资成本,助力美国经济的扩张,通过“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拉动就业。
但是,经济学一般规律告送我们: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QE系列也不例外。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虽然美国拥有全球“印钞税”,通过货币扩张来拉动经济、利用债务杠杆扩大信用投资,规模也有上限,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我认为,债务规模的最高限制在于政府、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的平衡点,美国次贷危机后企业即便有再低的融资成本,不愿意贷款投资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民选的政府在对待债务杠杆的问题上,跟企业的考虑是不同的。为了拉选票,执政者对债务规模可谓是多多益善,因为理论上讲政府开支的无限增加,可以无限拉动消费和就业,边际效应再低也是正的!可见,一个国家必须控制执政者的发债规模——而最佳的债务规模标志,则是公共投资的收益率与融资成本利率相同时。其中,公共投资的收益率需综合考量,主要源于财政税收收入的变化率和整个国家的GDP增长。对于今日的美国,无论是捉襟见肘的联邦财政,还是私有投资已经正常化的经济扩张,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显然都是得不偿失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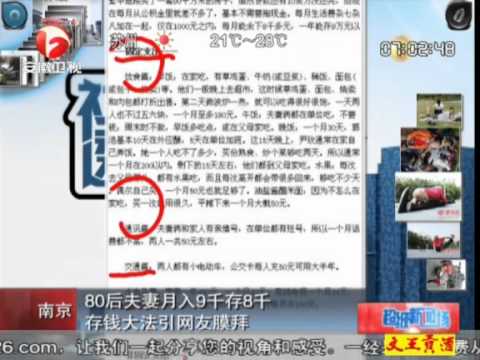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