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知名的海鲜餐厅,两位日本友人都是第一次来,在座陪同的还有L君,除了招牌的金瓜米粉、臭豆腐,还有干煎本港马头鱼,无一不是饕客们喜爱的美味佳肴。
我们的聚会既是送行也是迎新,即将奉派调回东京的村上与他的继任者鹈饲,都是我在《朝日新闻》担任客座研究员时的旧识。二○○四、五年,村上在经济部、鹈饲在国际部,他们是朝日年轻一辈的「中国通」,都曾被报社派到大陆各地学习为期一年的中文训练,有的甚至还前往重庆研读,以因应大西部的开发。
日本媒体的海外派遣向来很有制度,平均三年至四年一任,他们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多数被派过来台湾驻点的外籍记者,没有不喜欢台湾的,日本媒体亦是如此。从美食、风土、人情味到喧闹不已的民主政治,台湾社会快速翻转的节奏,以及关不住的旺盛生命力,每每令他们惊艳也称羡。
但是日本媒体内敛而冷静的性格,一如集体制约成性的大和民族,他们多半没有台湾媒体那般外放、生猛的热情,习惯保持距离的观察,不过,有时那样用心的观察,传达了一个外国人对这块土地直击的感受,却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在饭桌上,我提起村上曾写过的一篇报导,阅后令我颇为感动,有点像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味道。那是村上个人的亲身体验,他约略叙述一番,我后来再去翻箱倒柜,才知道那是他发表在电子杂志的随笔。
村上因为坐骨神经痛的问题,跑去一家整形外科诊所看病,医生嘱咐一些注意事项,劝他「最好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束前拿了一块贴布给他,还说「这次看诊就不收钱」,让他过意不去,但对方仍坚持不收钱。
那晚,村上参加一场聚会,而且是聚会的东道主。结果他发现自己的钱包掉了,赶紧回到先前搭计程车下车的地方,一位老人叫住他问道:「丢了钱包吗?」原来老人和他儿子是那里的清洁工,儿子已将钱包送派出所,而老人在那里等着。
村上赶去派出所顺利拿回钱包,他想亲自向对方道谢,拜托警察打了电话给那对父子,他在电话中表明想给一些谢礼(其实是送钱致谢,但村上在文中委婉地用「谢礼」代替了钞票),但儿子回答说:「谢礼就不用了,以后小心别再把钱包丢了。」
在这篇随笔里,村上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两件事只是偶然,自那之后,我一直在想应该如何回报这个社会。」
我读这篇题为〈这个城市的温暖并非偶然〉的短文时,心中浮现些许的骄傲,一种身为台湾人的骄傲。城市里的小医生,想必是体贴有爱心的人,即便不是视病如亲也绝非视钱如命,那平易近人流露的是台湾医疗之美;另一对拾金不昧的清洁工父子,虽然在都会中为生计打拼,却拥有崇高人格,他们懂得物归原主,也没有趁火打劫。
一天之内的两件事,让村上充分地感受到台湾人的良善,属于台湾社会最美的一面。即使村上离台在即,然而当他回忆此事时,仍不免赞扬再三,并感叹那是许多城市社会所没有的。
村上后来还写过台北市「自由巷」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以自焚抗议国民党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二十三年后,台北市议会跨党派通过决议,将自焚原址街道命名为「自由巷」,台北市长郝龙斌不仅同意提案,还亲自出席揭牌仪式。
在现场采访的村上,对于「自由巷」设立的始末应该知之甚稔,他知道当年被郑南榕猛烈批判的高官郝柏村就是郝龙斌的父亲,因此他特别提及郝龙斌在仪式上的发言内容─「非常尊敬郑南榕」。
村上在「自由巷」一文的结语,最能体现一个外国媒体的观察功力,他说,「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在台北也有人为了自由进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希望这样的历史能永远地留在人们心中。」
坦白说,我颇为这段简洁的叙述而折服,因为村上毕竟是个日本记者,台湾媒体报导「自由巷」揭牌的新闻时,多的是历史整理和政治分析,但俯瞰新闻事件时,却往往欠缺一定的高度与深度。
我因而想起自己生长的土地,作为一个媒体人,是否也曾有过那样深情的回首与敏锐的透视呢?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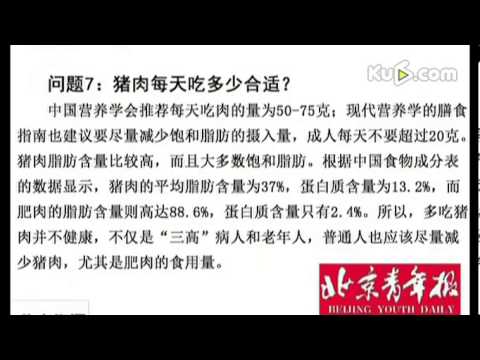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