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一位亡友的後續故事
三年多前的2006年8月,曾登過我一篇名為《我在勞改隊的老師》帖子,文中記述了1970年我剛進勞改隊時新結識的一位新難友的故事。
這位難友叫石炳富,同我一樣也是「現行反革命」,判刑8年。當時多虧他的熱心「教唆」,使我在集訓中得以順利通過了「交余罪」這道難關,後來我們成了好友。遺憾的是我和他「同窗」只有幾個月,1970年底,他被調往江蘇竹簀勞改農場,此後再沒見過。大約在76年前後,我從竹簀調來的一個難友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訊,據說是因病暴卒。我那篇《我在勞改隊的老師》,正是為悼念他而作。
文章登出後一晃三年多過去了。
2009年10月中甸某日,我在收件箱中忽然發現有份我的郵件,打開一看,一行字赫然映入眼帘:
「爺爺您好,我在您的作品《鐵窗十年4》中看見了一個令我熟悉的名字——石炳富,這名字和事件與我已去世幾十年的爺爺非常相符,從奶奶平時的話語中,我依稀找到了一線希望,您寫的《鐵窗十年》是真的嗎?」
我一下驚住了!
從對我的稱呼,以及略顯稚嫩的文筆判斷,這應該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所發。如此小小年紀,居然能從浩如煙海的網路文字中找到我三年前那篇文章,進而又順籐摸瓜找到我,這真令人有些匪夷所思。除了冥冥之中石炳富的在天之靈指引之外,我幾乎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釋。
我立即回覆了一個郵件,同時附上了我的姓名住址和電話、郵箱號,我再三希望盡快能見面,越快越好!
第二天傍晚,我家中電話響了起來,抓起話筒一聽,裡面傳來一個男子聲音:「請問您是方子奮老先生嗎?」
我說是的。
「您好方叔叔。我是石炳富的兒子,我叫石××。」
剎那間,我感到一股熱流直湧大腦,一下有些暈然。我有些不敢相信,四十年來遍尋未果的老難友後人,竟會如此奇蹟般從茫茫人海中現身,而且現在就在我手中電話的另一端!
不過,一個疑惑立即又在我心頭閃過。
在我記憶中,我清楚地記得石炳富曾親口告訴過我,他在1969年被捕後的兩個月,他妻子生了個女兒。後來在1970年底調走前,他又給我看過家屬接見時送來的一張照片,那上面他妻子懷中抱的確實是個小女孩,我還記得她頭上紮著兩個小小的丫角,一根小手指頭含在嘴中正甜甜地笑。儘管四十年過去了,這些往事我全然沒有忘卻。
可如今對方卻自稱是他的兒子。那個可愛的小女孩呢?
他簡單介紹了一下這些年來全家的概況,並表示熱切盼望盡快能見到我。我特意問他是否有姐姐或者妹妹?他說沒有,他是獨子。我在紛亂的思緒中未多說什麼,只是扼要的談了下當年和他父親認識的概況,順便提了下那張照片。我告訴他我會盡快去找他,臨挂電話時,我乾脆把見面時間定在了明天。
次日上午,我根據他提供的住址趕到了南郊的一個小鎮,下車後按他留下的號碼撥通了他的手機。問明我所處位置後,他囑咐我就在原地別動,馬上開車來接我。寥寥數語,聲音中明顯夾著按捺不住的驚喜。
這是個陽光燦爛的秋日,小鎮寬敞的街道明亮而又寧靜,全無城區的喧鬧雜亂,我靜靜立在道旁一株小樹下等他。我點起支煙剛吸了兩口,發現遠處有輛銀灰色轎車正在向我駛來,離我大約50米時,小車右轉向燈閃跳了起來,同時窗口伸出隻手在招,不用說就是他了,隨即我迎了上去。
就在他推開車門站在我面前那一瞬,我的眼睛不禁為之一亮:這確實是石炳富的兒子,絕對不會有錯!
高高的個頭,周正的臉龐,兩道粗眉下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張微抿的嘴,無一不像石炳富,特別是那道中部微微凸起、挺直的筆梁,簡直酷似乃父。不同的只是身驅比他爸爸魁梧,臉部也豐滿許多,不像當年老石那樣瘦削,那樣棱角分明。
我剛自報了下姓名,他立即伸出雙手緊緊握住了我,對我大老遠特地趕來見他們表示不過意,我趕忙笑著要他不必這樣。
他說話聲調有點像他父親,略微有點細窄,使人感到與他那魁梧的身型不太相稱。從他明顯帶著南郊一帶的口音判斷,應該是在郊區農村長大的。石炳富當年告訴過我,妻子是郊區菜農,看來老石兒子這些年一直同母親一道生活,目前的身份可能還是郊區農民。
稍經寒暄後,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家。
得知我心臟不久前曾做過手術後,他伸過強健有力的手臂把我一直攙上了五樓,我心中頓時充滿了暖意。
他的房子挺不錯,一百平米左右,寬敞明亮,整潔舒適,擺設也非常實用大方,看得出日子過的還不錯。在沙發上落坐後,我掏出錄音MP3放在了茶几上,笑著問他「不介意吧?」他一聽趕忙搖手:「不會不會,一切聽您的。」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長談。
我首先簡介了一下自己的過去,繼而講了當年結識他父親的經過。四十年前的事對我就像昨天剛發生一樣,對他無疑則是既遙遠又陌生的歷史,在聽我追述往事的過程中,他臉上不時閃過驚愕迷惑,有時也若有所悟的點點頭,更多的則是茫然。
他似乎也知道一點父親當年的事,據他說那是母親多年來無意中流露出來的。他曾多次問過母親,但母親一直不願多說,直到近幾年才簡單地告訴了他點父親當年出事的經過。至於內中詳情,好多事母親本人也不甚清楚。
接下來他向我談了怎樣找到我的經過。
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六歲,女兒十四歲。女兒自小聰明懂事,學習成績在學校一直是尖子,目前在當地一所中學讀書,每年都是前三名,多次受到過褒獎。講到這裡,他帶我看了他女兒的房間。
推門一看,迎面雪白的牆壁上那些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獎狀立刻吸引了我,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幾乎每學期都是第一名,另外還有不少歷年來參加市、區學習競賽的獲獎證書,看著看著,我心中不由越來越讚嘆這孩子真的不簡單!在介紹那些獎狀過程中,我注意到老石兒子那滿面的笑容,那笑令我有點熟悉,記得那年那個夜晚,他父親在臨別前夕給我看妻兒照片時也曾這樣笑過。
他女兒書桌上擺著一臺台式電腦,看樣子成色挺新,他走過去用手指輕輕彈了下屏幕:「要是沒有它,我們這輩子可能永遠找不到您。」
前不久,為了便於女兒查看閱讀課外學習資料,他特地替她購置了這台電腦,當時怎麼也沒想到,正是這台電腦,使他們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一個週末夜晚,由於白天功課不多,女兒九點不到就完成了作業,這時她打開電腦,像平時一樣隨便看了會新聞圖片,接下來也不知為什麼,她在Google搜索欄內敲了一下爺爺石炳富的名字。
事後她爸爸問她怎麼會想起來這樣做時,她有點支支吾吾地說,沒別的意思,只是出於好奇,想在網上查查有沒有和爺爺同名同姓的人。繼經細問,她說聽奶奶不止一次提到過爺爺的事,隱隱感到爺爺的早逝肯定內有隱情,但又不便追問,於是抱著一種僥倖,看看能否通過神通廣大的網路搜到一點有關爺爺的信息。
誰知搜索的結果令她大吃一驚。
在Google「石炳富」的辭條中,竟有近十條相關內容和我已發帖在網上的文章掛在一起(《鐵窗十年》、《南京慧園裡6號的母子冤魂》等)。她沿著一系列鏈接很快讀了我的原文,然後立即告訴了爸爸。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情節。
聽了這段經過,我不禁有些迷惘。
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生活在一個挺溫暖的環境中,奶奶疼,父母愛,感情上從來不缺什麼,可她卻唸唸不忘從未見過的爺爺,這究竟是為什麼?對此我又該如何解釋?當她在Google搜索裡鍵入爺爺名字時,難道僅僅只是為了滿足一下好奇心?當她知道了爺爺不幸遭遇的情節梗概後,她又會作如何感想?
當我自言自語道出這些疑問時,老石兒子將目光緩緩移向了窗外,一邊若有所思地微微點頭。
「您說的也正是我和我愛人所想的,我們也搞不太懂女兒的真正想法。為了怕影響她學習,我們只是要她別再多想爺爺的事了,其它沒多說什麼。至於她究竟怎麼想,我們沒進一步追問,畢竟是中學生了,我們得允許她有自己的獨立想法。」
稍停之後他輕輕嘆了口氣:「想來想去,只能認為是她爺爺在天之靈暗中啟示了她。」
這正好同我接到他女兒郵件時的想法不謀而合。
「那末,是誰提出來給我發郵件的呢?」我問。
「是女兒提出來的,我們同意了她。郵件的內容也是她自己起草併發送的。我和她媽文化都不高,還不大會搞這些玩意兒。」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爾後我們的話題移向了他爸爸的死。這時他告訴了我一段有關他爸爸之死的情節。
大約是在1975年夏秋之際,某天石炳富傍晚下班後去開水房打開水,管開水房的犯人同老石很熟,兩人攀談了一會,開水灌好後,老石拎著兩隻水瓶沿回監房的路走去。據那位管開水房犯人事後說,就在老石離開水房七八十米遠的拐彎處時,突然一輛軍用吉普嘎地一聲停在了老石身邊,緊接著車上跳下來三個人,一把將石炳富架上了車,然後向遠處疾駛而去。開水房犯人覺得有些蹊蹺,隨即偷偷跑過去看了一下,發現那裡周圍空空蕩蕩,只有老石的兩隻竹殼水瓶倒在路邊,瓶膽碎片撒了一地。
自此之後,一連幾天再沒見過老石。沒隔多久,勞改隊傳出消息:石炳富因突發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身亡。
有關老石死亡的具體詳情,沒任何人知道。
開水房那個犯人聽到此事後,立即把石炳富的死同那天被軍用吉普帶走的事聯繫了起來。作為一個勞改多年的老犯人,他懂得閉緊嘴巴的重要性,因而對任何人都沒提起過。直到好多年後,當老石兒子通過一個偶然機會找到他,而他本人又感到自身安全不會再受到威脅時,才將當年他親目所睹的那一幕說了出來。這時老石死去已快三十年了。
老石死後,他妻子接到了老石原工作單位轉來的一份勞改部門通知:
×××:
石炳富原係我單位服刑犯人,197×年×月×日因突發心肌梗塞不治身亡,後事已由我單位就地處理。特此通知。
江蘇省第××勞改隊
寥寥數十字,幾行例行公事行文,一個「現行反革命犯」的生命記錄就這樣草草畫上了句號。
當老石妻子問及丈夫死亡具體情況時,得到的是一句惡狠狠的呵斥:「人死都死了,還問那麼多幹什麼!」
直到近四十年後的今天,老石死亡的詳情沒人知道。
談到這些事時,老石兒子堅持認為他父親被那三個軍人帶走後,出於某種需要,最後被他們秘密處決了。
可我斷然否定了他這種看法。
我告訴他,秘密處決在49年後的中國不是沒有,但極少使用,而且對象僅限於高層內部權力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對數以千萬計的「階級敵人」,中國當局歷來總是公開屠殺,不但公開,而且還會開足輿論機器,配以大張旗鼓的高調宣傳。
世界上只有那些對手中權力不那麼絕對自信,同時多少還殘留一點理智的政權,才會把秘密處決當成常規手段使用。這是因為他們對大肆公開殘殺敵對分子多少有些心存顧忌,從而不得不採用這種相對隱蔽的做法。
中國則不然,中國有對殺人感到「其樂無窮」偉大領袖的絕對領導,有冠冕堂皇「放之四海皆准」的殺人理論,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有將近地球四分之一人口被洗過腦的「革命幹部群眾」,這就使得中國的統治者有了足夠的底氣,敢於肆無忌憚地公然放手廣開殺戒,他們根本不屑以秘密處決方式來解決「階級敵人」,他們嫌那樣做太小家子氣!
作為成千上萬「現行反革命」之一的石炳富,只是個毫不起眼的小不點,他根本不配享有被秘密處決的資格!
從另一方面看,既然只判石炳富八年徒刑而沒一殺了事,這表明他這條命多少還能派點用途,一個年僅三十來歲且有一手鉗工技術的勞改犯,對建設「社會主義」而言,畢竟要比一頭牛馬更具實用價值,平白無故殺掉這條高級牲口,不符合革命利益的需要。
一句話:當局沒有任何以秘密處決方式從肉體上滅掉石炳富的必要!
那麼石炳富究竟是怎麼死的呢?
我在綜合比較各種可能因素後,認為他極可能死於一場「誤殺」,或稱之為一個「意外」事件。
以下情況就是我的推測:
大約是他某位朋友(或同案)有些事牽涉到了他,有關部門來找他瞭解情況,他不僅不「積極配合」,而且態度相當「囂張」,以致審訊人員出於「革命義憤」,對他採取了審訊過程中慣用的「革命手段」,而老石不太壯實的筋骨又未能抗的住,結果就導致了一場「誤殺」。按公檢法內部說法,通常將此稱為審訊人員一時「失手」造成的「意外」事件。
儘管事先並不打算要石炳富的命,但「誤殺」也好,「失手」也好,人死了卻是不爭的事實。一個活蹦蹦的人突然莫名其妙的死去總得有個說法,於是「突發心肌梗塞」就成了最好的解釋。這個病,老、中、青、幼不同年齡段的人都適用,用它堵住各種別有用心者的嘴巴顯然再也合適不過。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雖然不怕任何「壞人」鑽空子,但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往往總是考慮得很周密的。
老石兒子聽了我的推測後說,他找到那個開水房犯人時,那人好像也有點這方面意思,只是沒我分析的這麼透徹。
當然,這畢竟只是我的推測,其中具體內情到底怎樣,對我們來說只能是個難解的謎了。即便將來有一天出現歷史清算,恐怕也很難查清,中國這種事實在太多了!
接下來,我向老石兒子提出了另一個心中之謎:
「當年老石給我看的那張照片上明明是個小女孩,後來怎麼成了你呢?」
「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昨晚您在電話裡談起後,隨即我問了母親,她這才講了點當年的情況。
「那時我還在吃奶。父親抓走後,母親帶著我回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住在棲霞(註:南京郊區),當時那裡政治運動搞得比城裡還熱火,城市裡表面上還講點政策,在我們那裡簡直就是無法無天,想怎麼搞就怎麼搞,周圍好多地主富農反革命被活活打死了,家屬子女也一起跟著遭了殃。母親帶我去了後,很快便被發現是「現行反革命」家屬,沒幾天有人放出了風:‘一個反革命哪能讓他有後代?他的後代將來肯定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後患!趁草鋤了這根小反革命秧秧(當地土話,即苗苗的意思),決不能讓小反革命將來接老反革命的香火’!」
說到這裡,老石兒子有點激動起來,眼裡明顯露出了恨意。我輕輕拍了拍他的手,站起來給他沏了杯水。
「外公外婆和媽媽聽到這些風聲後,嚇的不知如何是好,母親當時只是緊緊摟住我哭。她曾想過帶著我遠逃外地,可當時全國到處一樣,一個弱女子抱著個吃奶孩子往哪藏呢?想來想去,想去想來,最後外公勉強想出了個辦法:從即日起,全家對外謊稱我是個女孩,為此特地替我梳了兩根小辮,衣服鞋襪一律按女孩打扮。農村歷來重男輕女,即便那些運動積極份子,多少也會認為女娃成不了大事,一個反革命女崽子比起男崽子來,對革命的隱患要小的多。
「幸好的是,後來沒人來認真核查我的性別,讓母親和我總算逃過了一劫。直到運動風頭過去一兩年後,我才又成了男孩。你看過的那張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當時的我。」
原來是這樣!我怎麼也沒想到,那張照片後面竟然還隱藏著這樣一段故事。更令我感嘆的是,當年石炳富居然也瞞過了我。
幾十年來,我對無產階級專政可謂太知根知底了,即便如此,我還是對這種斬草除根、不留後患的革命手段有些驚訝。望著眼前高大魁梧的老石兒子,我不由為他在襁褓中能逃過那一劫深感慶幸。
「那張照片現在沒有了吧?」明知希望不大,我還是抱點僥倖心理問了一句。
他搖了搖頭:「早就沒有了。當時一共兩張,一張給了父親,另一張丟失很多年了。母親記得當年確實在給父親的那張背面上寫過幾個字,不過她早忘了內容。」
最後他介紹了一下後來的事。
1979年3月,經南京建鄴區法院複查,撤消原判,宣告老石無罪。對他死在勞改隊一事定為「正常死亡」,結果補了六個月原工資,加上喪葬撫恤,一共給了2174.7元;兩年後的1981年,又把他的死改為「非正常死亡」,並根據規定對尚未成年的兒子及老母親分別按月發放生活津貼。
說實話,這在我認識的死去難友中,身後補貼算是最好的了。
老石判刑後,妻子帶著孩子一直在苦苦等他,到1975年時眼看老石刑期已經大頭朝下了,誰知卻一下接到了丈夫的死訊。為了孩子,她在76年與另一位男子重新組成了一個家庭,後來又有了一個女兒。老石兒子的這位繼父在糧管所工作(在農村稱之為吃「皇糧」的),全家人靠他那點微薄的工資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談起這位繼父時,老石兒子滿懷深情地告訴我:「他待我非常好,就像對親生兒子一樣,我們全家永遠都會感激他。」
本次採訪結束前,老石兒子帶我和他繼父見了個面,老人身材不高,皮膚略黑,一看就是位秉性忠厚的好人。照常人眼光,我這次採訪也許使他多少會有點不太舒服,可他對我表示了真誠歡迎。望著他與老石兒子併肩站在一起親密無間的神情,我不由為石炳富的妻兒能找到這樣一位好人深感欣慰,老友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中午我們在他家樓下一處小飯館吃了頓便餐。應我的要求,飯後他開車帶我去見她女兒。
他女兒就讀的中學挺不錯,一進寬敞的大門就是400米跑道的標準足球場,遠處幾排教學樓白色的外牆在午間陽光下潔白耀眼,比起城區中學校來,校園算夠好的了。
經門衛聯繫後,我和老石女兒在校門口見了面。孩子身材比她同齡人要高些,只是略顯瘦削。白淨的臉上很嫻靜,經她爸爸介紹道了聲「方爺爺好」後,一直沒說話,性格看來似乎有點內向。我不想對孩子當面提她爺爺的事,只是簡單問了問她學習情況。在我們對話過程中,老石兒子柔和的目光一直沒離開她,看的出爸爸非常鍾愛這個品學兼優的女兒。
考慮到午休時間有限,沒談一會我和老石兒子帶著他女兒一同去了他妻子的工作單位。她在一家合資企業打工,只有中午休息時才能抽點空會客。
她是位身材嬌小的湖南女子,兩道好看的眉毛下,嵌著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由於正在當班,她穿著一身淺蘭色工作服,顯得既精幹又樸素。她知道我今天來意,一見面就笑著對我老遠趕來表示感謝。由於上午和老石兒子已經談了好久,我沒再提老石的事,只扯了些她老家湖南的風土人情。她熱情地勸我一定吃過晚飯再走,說要做點湖南口味菜請我嚐嚐,我笑著婉拒了她。
回來的路上我誇老石兒子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他沉吟片刻後說,這也許是父親在天之靈保佑我們所致吧。」
臨別前見到了老石妻子。上午我曾表示過想見她,當時她沒明確表態,午飯後她來電話表示同意見我。他和老伴的住處離兒子家很近,在她樓下一塊空地處我們見了面。
儘管人們都懂衰老不可避免,可當我見她第一眼時仍難抑制心中湧起的強烈感慨。滿頭花白的頭髮,眼角深深的魚尾紋,這與當年照片上那位清秀美麗少婦的反差實在太大了,令人怎麼也無法相信居然會是同一個人。四十年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只是彈指一瞬,而對一個人容顏的磨蝕竟會如此強烈,我不由暗暗長嘆了口氣。
老石兒子向母親道明我的來意後,她勉強笑了一下。我先提了那張照片的事,繼而又表示想瞭解一些當年老石被捕的前後經過,她聽完後沒立即作答,稍後才微微皺了下眉說:「唉,那都是些幾十年前的舊事羅,還提它們做什麼?」大概是怕過於冷淡我緣故,想想又補了一句:「對不起啊方……方老師,不是我不說,好多事我真的記不清了。」老石兒子沒在意母親的冷淡,向她追問是否真的忘掉那張照片背面上的那些字了?她埋怨地看了一眼兒子說:「快四十年了,我哪能記得啊?」
顯然,老太太不願重提舊事了。這使我聯繫起剛才初見面時她有些勉強的神情,尤其是眼神中那種難以掩飾的警覺。我隱隱感到這次我的來訪非她所喜,之所以勉強同意見面,大概只是不忍拂卻兒子的興致。
到此,我已沒必要再重提舊事了。想想也是,經歷了新婚痛別,丈夫慘死,再加上幾十年來種種精神折磨和生存壓力,老太太這些年來心路歷程的艱難可想而知,如今確實不該再給她已經歸於平靜的心再掀波濤了。
臨別時我舉起相機準備給她拍張照留念,一見要照相,她趕忙側過臉去並伸出手擋住了我:「別拍,別拍,人都老了,還拍它幹什麼?」老石兒子見我有點尷尬,趕忙抱住她的肩安慰她:「方叔叔沒別的意思,只不過替你拍兩張照片做個紀念,你放心,他不會給別人看的。」見兒子如此說,她這才將臉轉了過來,一邊用手理了理頭髮,一邊又有些緊張地關照:「就拍一張啊,可千萬不能發到那個……那個什麼網上去啊!」
望著鏡頭前這位老姊妹佈滿皺紋的臉,一種混合著同情,憐憫,諒解的複雜感情立即攫住了我的心,我終於沒按快門並放下了手中相機。我不能給她的晚年再增添任何一點煩惱。
道別後我正轉身之際,她突然叫住了我:「謝謝你來看我們啊。你年齡也大了,一定要多保重身體。還有……你其它方面也要注意啊,別看現在比以前鬆了點,說不定哪天又會來什麼運動……」聲音中既有感激,也有關心,更多的是劫後老人難以消弭的餘悸,我趕忙笑著打斷了她的囑咐:「我知道,我知道,我會注意的。您也多保重,再見!」
走了好遠我回頭看了看,她還立在那裡注視我的背影。
我想,我再無必要來打擾她了。
老石兒子堅持要駕車送我回南京城,我謝絕了他。今天的來訪已耽誤了他不少時間,我可不想再白耗他幾個小時,隨即我擠上了一部郊區客車。上車前他一再要我常來作客,我滿口答應了他。但我知道這只是客套而已。親眼看到老難友後人有正常平靜的生活,我已很滿足,我不會再來了。
剛剛上車,一位年輕姑娘站起身來給我讓了座。曾幾何時,都是我給別人讓座,不知不覺間自己也到了別人給我讓座的年齡了。老石要不死的話,今年該是七十三了,當年那個告別的夜晚,誰想到四十年後已成古稀老者的我會有今天的此行啊!旦願我今天探訪的一家老小永遠都能過上正常平靜的生活吧,旦願老石和我親歷的那些噩夢永遠不會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吧,但是,我這點對人生最起碼的祝願又能否真正得以實現呢?我不由咀嚼起剛才臨別時老石妻子的那段囑咐來。望著車窗外秋日燦爛的陽光,我陷入了沉思。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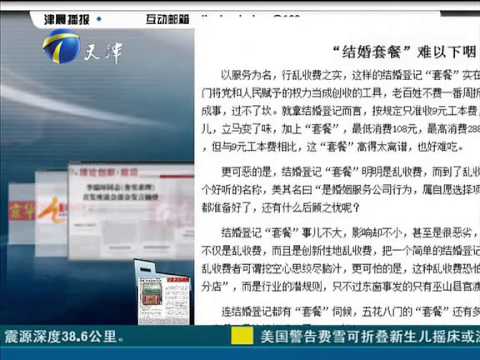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