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没有别的文艺节目,只能听样板戏。京剧本来就不是人人都爱听,八个样板戏轮流听了一遍又一遍,国人也都腻烦了。创作样板戏是政治革命,看听样板戏是政治任务。只有反复学习反复听。各地基层的业余剧团也组织起来学演样板戏,部队师团一级都组织了宣传队,一水儿演京剧样板戏。一天到晚样板戏,公众的厌烦情绪当然要表达。不能公开反对,渐渐地,全国上下编派了不少关于样板戏的笑话。
我记得有几个段子传说较多。
一家剧团演出《红灯记》,演李玉和的演员太高,演李铁梅的太低,李玉和出门,铁梅要给爹戴上围巾,不料李玉和低头弯腰,铁梅抡起围巾怎么也够不着,戴不上。李玉和只好临场发挥,接过围巾说:“还是自己来吧。毛主席说要自力更生嘛!”台下大笑。
外出坐台一般三天,剧团不能只演一场,几个样板戏轮换上演,演员连着轮换角色,难免出错。《沙家浜》演胡传魁的在《红灯记》里演鸠山,“智斗”一场,要问阿庆嫂:“我问你这新—四—军?”演员串到《红灯记》里去了,胡传魁逼问:“我问你这密—电—码!”传出来又是一个笑话。
演样板戏是政治任务,演出叫做“学习革命样板戏,演好革命样板戏”。演员都很紧张,生怕出错。越怕出错越出错。《红灯记》里对李玉和用刑以后,日本宪兵要出台回报鸠山:“报告队长,李玉和宁死不招!”演员一紧张出了错:“报告队长李玉和他招了!”一下子满堂惊愕。多亏了鸠山转圜,“像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怎么能招了?你搞错了吧?再问!”救场是救了场,哄堂大笑,这可是政治错误。
《智取威虎山》的笑话最多,大概因为排演的多。杨子荣打进匪窟,座山雕要考一考他的本事。在威虎厅一抡手枪,打灭一盏吊挂的灯。下面该是杨子荣要过枪,一枪打灭两盏灯,众匪徒接着大叫“一枪打两,一枪打两!”后台有管效果的,拉这个闸灭一盏,拉那个闸灭两盏。太紧张了偏偏出了事,“啪”地枪一响,他一把拉了总闸,全场漆黑。座山雕连忙救场:“胡彪好枪法呀,保险丝都打断了!”整个大厅笑爆了。
我得声明,以上这些笑话,有些是演出中间的真事儿,大多数都是编的,算是那时的编创。故事在编创过程中越编越圆满,越变越精致,越传越热闹,在文革期间严酷的政治生活里,这些笑话可谓调味剂,当年那一代人都记得。
有些笑话生命力旺盛,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座山雕问杨子荣:“听说许旅长有两件珍宝?”杨子荣答:“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刀是什么刀?”本来回答“卷毛青鬃马,日本指挥刀!”现在人们常常接答:“吹牛拍马,两面三刀!”这当然是对现实人际关系的不满。
我们现在说这些笑话,仿佛很轻松。文革中间出笑话,那可是政治问题,轻则批评处分,重则撤职开除。人们整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错误。因为演样板戏出错受了处分的不乏其人。1974年在首都剧场看《平原作战》,演小英的李维康在幕后一句“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跑了调,全场大笑。陪我们看戏的首长忧心忡忡,担心受处分,一场戏看得没有情绪,至今记忆犹新。
文革的政治高压,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特别荒唐治民手段。本来一个戏,大家不满就不满,不演就不演。可是那十年,没人敢不演,没人敢提意见。不满情绪不能严肃表达,只能选择笑话这种形式,在戏谑中发泄内心的不满。文革中间几亿人万马齐喑,另一方面,这种笑话式的隐形创作也不可忽视。想想那十年,几乎每一个运动,都有相关的政治笑话流传。这实际上是对高压政治的一种曲折的反抗。鲁迅曾经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在那个年月,冷嘲热讽最能消解所谓积极意义。对付庄严的假面,撩拨一下,出他一个洋相,高头讲章政治课变成一道笑料,也是国民的批评智慧吧。
哲人说,笑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能力。但显然人不能随便笑,为什么笑、笑什么和笑谁是非常不同的。文革时期思想戒严,公共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中没有笑话的位置,导致笑话私下讲传盛行,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这当然表现了那个时期社会的公共话语形态,应该受到历史学的重视研究。
近几年我们经常遇上恶搞。样板戏的笑话,也属于文革中的恶搞。面对威权,个体的无力无助往往可以从集体的戏谑中得到解脱。全民恶搞简直就是全民示威,戏谑的口气传达的是反抗的火星,极权政治应该从中感受到压力。诗可以怨。政治笑话无疑是民风民情的巧妙表达,却也是无奈的表达。哪一个时期政治笑话创作繁荣,那个时期国家肯定出了问题。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和1960—1970年代的我们,是政治笑话传播最热闹的地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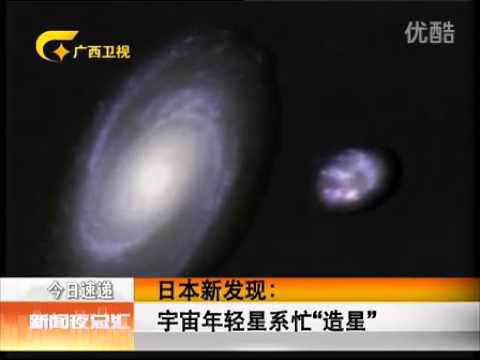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