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合成图)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但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便开始讲话,那样子颇为神秘──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员,他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x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劫走李九莲。(按:这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而制造的东西)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
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
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屌?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像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没话讲,我们的信仰不同’。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女人……”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里面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像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像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像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与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拚命调动起“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的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像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登”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白骨精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像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像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像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一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拚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像是什么在撕扯,又像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也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一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
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X用。一到关□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杓,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一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一边嘴里骂着,一边拉开枪机,黄珵珵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像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采……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像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辟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像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像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份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
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x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与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像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像撕扯什么,又像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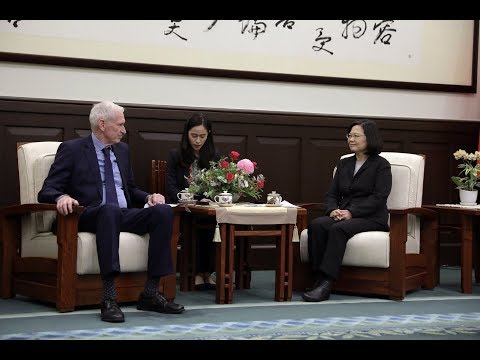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