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右派50年
一個酷愛籃球的高二少年,陳宗海,因為一個不高明的玩笑,從此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反革命團夥罪名送監。十年農村改造,摘帽後草草退休,荒誕一生。
當孫子還是賴在陳宗海懷裡使勁撒嬌的年紀,他仰起腦袋,向瘦高的老頭髮問:爺爺,你年輕時幹啥呢?—我呀,我在義大利踢足球啊。爺爺你說個義大利語唄—拉密密塞腳溝,這是發界外球。
他是胡謅的。如今孫兒業已成年,那個俏皮的謊言仍時常被拿出來,供大家哈哈一樂。80歲的陳宗海他愛看《百家講壇》和NBA,尤其是後者。42英吋的液晶屏幕裡,大洋彼岸激盪的驚心肉搏,老爺子看得如痴如醉。
與兒孫們聊天,多是家常細瑣,陳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長者的角色。他記得當年父親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嘮叨,大事平心靜氣講。那麼,自己的過往算什麼呢?算不上大事。晚輩們不問,他也懶得提。大家只是隱約知道,老爺子年輕時當過「右派」,送到夾邊溝,吃過苦頭。
他很少出門。如今保持走動的還都是初中時代的朋友,人家來叫,他便配合著過去。坐在他們中間,他覺得自己永遠是一個陪聊。對於社交,他提不起一點點興趣來。
去年冬天,陳宗海找一個中醫大夫看胃病。大夫說,你這麼大年紀,性情還這麼暴躁,是生氣造成內消化不好。陳宗海抱怨:我是抑鬱症,過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
他盡力避開生活裡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誕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運的,」陳宗海說,「我不偷不盜,怎麼能有牢獄之災呢。怪,哎呀,我的媽,真可笑。」他搖搖頭,兩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輕時手欠,信手在報紙上塗上的那幾筆,毀了一輩子。
眼淚
那些生命中最絢爛的年華,已如祁連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鹼地,卻在百年后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他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如今他做到的好夢,多半是自己在籃球場上奔跑的身影。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在可供揮霍的青春裡,學而優則仕一類的夢想被遠遠拋在天邊。朝鮮半島的戰火燒到邊疆,中國出兵。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承認自己並無太多「政治覺悟」,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
或許,以後去當個運動員吧,他想。但很快,他還是被裹挾進強大的政治機器。
毛岸英戰死的消息從遠方傳來,校園裡人們竊竊私語,小心猜測著中南海的反應。有天,他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他看,他為他感到難過,老年喪子的哀痛彷彿一樣籠罩著他。他拿出鋼筆,給畫中人添上了幾滴眼淚。
他被指為思想反動,污蔑偉大領袖。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在檢討中他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污辱。批判會上,積極份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勞教
那個時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伙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他幾家砂鍋作坊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人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裡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六十元。
進入1956年,形勢加速變幻。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里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裡,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忿:我只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捲而來。給毛主席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
他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裡,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學校有個反右積極份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裡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家裡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最多一兩年。
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裡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裡,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來越渺茫,這年國慶過完,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俞兆遠看陳宗海累成這樣,便跟隊長建議,把陳調去放水組。那是個輕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時可以在菜地裡偷莊稼吃。
「偷著吃,不偷活不了,」陳宗海說,「可能我比別人偷得還多一些。」陳宗海偷大田裡的東西,土豆、洋芋、糜子、麥粒,一切能吃的都偷著吃。但他有個原則: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別人的東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裡,陳宗海跟俞兆遠閒聊。俞兆遠無意中說起,老家有人過來探親,說城郊農場勞改犯的生活比這裡「右派」好得多。勞改犯每天只勞動八小時,每人每月的口糧是四十斤,這比那卻是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量,口糧卻只有二十四斤。那邊餓死犯人的事比夾邊溝少得多。
陳宗海怦然心動。他尋思能不能自己也換個身份—變成犯人去城郊農場。
五月的一個夜晚,他打死了一頭豬,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計畫是,來一次刑事犯罪,夠判刑,一兩年就成。但此事竟無人發覺,陳宗海又喜又憂。喜的是吃到豬肉,憂的是獲罪計畫沒能成功。他又偷了一隻羊,還是沒人來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夾邊溝「右派」轉移到明水。國慶節時,農場來了個小個子年輕警察,他對陳宗海說,你們怎麼還休息呢,要好好幹啊。陳宗海隱隱覺得此人有些蹊蹺,他玩笑回應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給忘了。
過了幾天,警察把陳宗海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蘭州市城關區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陳宗海。
大組長已經把陳宗海的行李拿來,警察給陳戴上手銬。第二天陳被送上火車,押回蘭州。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後,陳宗海被宣布五年勞改。
這下算是了了陳宗海一樁心願,此時每天周圍都有幾十人在飢寒交迫中死去,他終於可以不在明水農場等死了。但自己怎麼就「反革命」了呢?
來夾邊溝前,陳宗海與夜校的兩個同事合了張影。照片背後寫了一行字:讓我們的友情如森林長青。任憑它驚濤駭浪,也阻止不了我們對真理的信念。陳宗海把照片掛在家裡,過了幾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舉報,照片後面是他們的反革命誓言,三人裡通外國,準備發展組織逃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陳宗海大怒:哪個王八蛋造的謠,想把我往監獄送麼?
兩年後陳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進了監獄。進夾邊溝後,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監控中。公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陳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組織,判決陳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兩位同事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種驚喜交錯的荒誕感中,陳宗海開始了納鞋底的勞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們處得舒服,但監獄裡10年也死不了,夾邊溝再蹲1個禮拜也許就挂掉了,陳宗海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兩個月後,合議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決,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陳宗海回到家裡。老母親看著兒子心疼得直搖頭,眼淚巴拉巴拉掉,一句話說不出來。
對於「右派」來說,並非所有人回到家裡都能迎來笑臉。兩年時間妻離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遠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離婚。理由是,俞兆遠在夾邊溝吃慣了偷來的生糧食,回家兩年,還要偷面櫃裡的苞谷面吃。鄰居們都說,俞兆遠的女人不讓他吃飽,逼得丈夫偷家裡糧食。
下鄉
麻煩很快又找上了陳宗海。居委會讓陳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政治」,月月寫思想匯報。從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學習一直沒有間斷過。
陳宗海買了一輛架子車,加入街道組織的車隊拉貨度日。拉車第一天,陳宗海心裏百味雜陳,自己曾經也是個幹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騙人,憑勞動吃飯嘛。一個月下來他能拉到158塊,扣掉稅款,剩了104塊。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架子車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陳宗海作為黑五類分子被遣往農村勞動。孩子老婆還有那輛架子車,一塊交給了70歲的父親大人。他的下一站皋蘭縣青白石公社,是陳家的原籍。距離蘭州城100華里(1華里=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隊裡只有他一個「右派」,周圍都是農民。大家都知道他給毛主席畫了眼淚,倒也沒人因為「右派」欺負他。農業社會的古樸和務實,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壓的恐懼。陳宗海與所有人一樣下地干農活,一起吃大鍋裡的稀飯,他與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經歷了短暫的陌生後,村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過陳宗海遞過來的煙,一起吞雲吐霧,上天入地胡侃。
陳宗海卻暗暗為他們悲哀。「我現在就想啊,人確實好騙。在農村裡蹲了10年,上面說他們是貧下中農,工人農民是領導階級,他們就高興得整天在那裡刨地。」
反倒是幾月一次的探親,卻慢慢從興奮變成了沮喪。穿過一路枯燥的風景,陳宗海蹬車回到蘭州家裡,同學和親戚已中止了與陳家的來往,鄰居們閃爍微妙的眼神讓他惶惑。他更願意蹲在農村,在那裡,沒人在乎他是一個「右派」。
上世紀80年代時,他看到謝晉的電影《牧馬人》,不禁啞然失笑。電影主人翁許靈均也被打成「右派」,來到西北牧場勞動。老牧民視他如至親,一個漂亮的姑娘還看上他,倆人有了一片無憂無慮的小世界。「我們哪有那樣的好運氣!」陳宗海感慨,「農民只是佔小便宜,所以忘記了階級鬥爭。」
這次陳宗海不再敢預計歸期。每年大隊開大會,讓群眾評議陳宗海一年的表現。「他沒幹什麼壞事,干沒幹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這麼說。每年評審報上去,結果卻總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後,陳宗海不禁懷疑還有沒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問:「右派」帽子真的是終生的麼?
毛澤東逝世時,陳宗海跟家裡找招呼:啥也別說。大隊開追悼大會,不讓陳宗海參加,「其實我也不想參加,」陳宗海說,「我覺得沒了他事情會好一些。」他曾被掛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請罪。但他覺得這算不得什麼,「‘文革’於我有利,毛這個事毀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遠走在蘭州街頭。路邊電線桿上的大喇叭裡開始播出那次著名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俞兆遠漫不經心聽著,他覺著越聽越入耳,最後他趴在欄杆上,豎起耳朵聽完了全文。公報中有一段話,講到了平反問題:
會議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
俞兆遠想:這下有出頭的日子了。
實際在半年前的4月5日,《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已獲中共中央批准,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問題在之後的幾年裡陸續完成。
1980年10月,陳宗海蓋完最後一個章,他拿著畫滿各種遷入遷出標記的戶口本回到家裡。從此他再不是一個「右派」。他拿到一千塊錢的賠償,這大約相當於當時工人一年的工資。錢拿到手,他總覺著是一筆意外之財。
俞兆遠也拿到6000元賠償。周圍人都說,老俞發財了。俞兆遠說,「我窮的時候誰都不上我門,現在什麼事都來找我,借錢?算了吧。誰都不借。」
很多人沒有拿到任何賠償,這是個傷腦筋的問題。另一位「右派」劉光祖在退休後的十餘年裡,堅持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資奔走多年,他找單位、市委、省委……寫過無數次申訴,無人能為此事負責,或者給出解釋。2007年,老人在病中鬱鬱而終。
父親勸陳宗海,如果對賠償定案不滿意,可以寫申訴材料。陳宗海搖搖頭:我沒有啥意見,有補償就不錯了。弄不好再加個處分怎麼辦?近幾年,關於「右派」索賠的呼聲開始多起來,陳宗海微笑搖頭:我沒想過要賠償,沒戲的。
陳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經四十九歲。此時距離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彈指一揮間過去了。熟人說:老陳你現在怎麼這麼不修邊幅了呢,五十年代還挺時髦啊。是的,那會兒還能花半月工資去買雙漂亮的小方頭皮鞋。在農場、監獄、農村,哪裡還有講究的條件?現在呢,老了,沒心情了。女兒給他買衣服,他不願要。他覺得對家裡虧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種交接,在陳宗海摘帽半年後,85歲的父親撒手西歸。在之前的20年裡,父親一直在打著零工幫陳照顧妻兒,這個家庭終究得以保全。在陳宗海遙遙無期的等待時光中,他的頭腦中一直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親過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干了九年小學教員,陳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過的所有生計一樣,人生的最後一份工作也沒能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沒有那個事,我可能就是個運動員。」他喃喃道,眼中掠過一絲遺憾。
2008年,陳宗海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廣告:舊德的精彩。他並不知道這也是一本講「右派」的書,但出於對「舊德」的興趣,便上街買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卻感到強烈的隔膜。書中主角們是他在學生時代耳熟能詳的「大右派」,他們在運動後依舊開著小車,住著大宅。他開始為半世紀前的那場運動感到困惑:「‘右派’與‘右派’簡直相隔十萬八千里,反右—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幾乎所有的接受採訪的「右派」,都會特別說明一句:平時,我很少提起這些事的,這些經歷總覺得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人年紀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遙遠的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俞兆遠怕說夾邊溝,「一提這個事,就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他每晚睡覺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帶著幾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遠跟家人來北京旅遊,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俞淡淡地看著那位靜臥的老者,在心裏說:你這個老人家,過去制定的政策,不但對我不利,對好多知識份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遠拒絕給自己做壽。摘掉「右派」的帽子後,他越發覺得人生虛無。有個熟人60歲做壽,過後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壽宴上那些紅花綠花,瞬間就變成了靈堂裡的白花。
當年是誰揭發了陳宗海?陳說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倆人各自帶著妻子,在蘭州街頭面對面撞見了。彼此微微點了下頭,便擦身而過。走出去幾步,陳拉拉老婆,「這就是當年揭發我的人。」他回過頭,那人也與女人回頭看他們,像是說,看,那就是給毛主席畫眼淚的傢伙。
恨他麼?不恨,陳宗海說,我一點都不怨他。從此他們再未碰面。
(本文略有刪減)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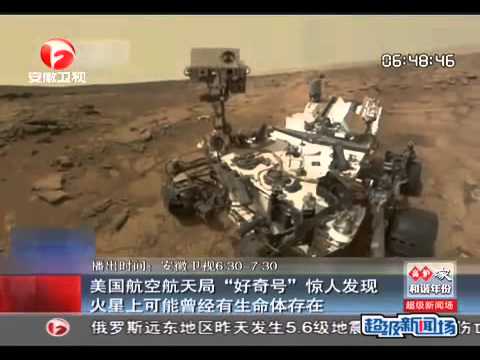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