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騫總共率領了一百多人,滿懷豪情的手持旌節,踏上了他這一生顛沛而傳奇的命運之路。(網絡圖片)
少年英雄破荊棘 漢使西域坎坷行
是什麼樣的膽識和什麼樣冒險犯難的血液,會令一個少年郎遠赴關山、披星載月,在對前程毫無所知的情況之下,只憑著理想與勇氣,就能身懷莫大的使命,前進到那處處異域與詭譎之地?
當時亙古天頂靜夜的星辰為年輕的張騫指引了方向,身旁的胡奴嚮導對此行忠義相幫,再加上週圍這一群立於荒漠高山之上的青壯;這百餘夥伴所組成的小小隊伍當時由中土出發,一路伴隨著張騫,卻在際遇的作弄下永世無法回鄉……;命運竟然就以這個在歷史長河裡毫不起眼的蒼茫片段,悄然開啟了這日後絲路文明所留下的這千絲萬縷的記載,並在中華文化的發展史上漸漸織就了一座座永恆的豐碑,一直到千秋萬代之後,當年張騫所歷之絲路,仍舊閃爍著華夏文明的榮耀與光芒。
張騫的生年不詳,他與漢武帝是同時代的人,大約於西漢的文帝后期出生於成固一地(今陝西省城固縣)。據說他體魄健壯,性格開朗,從小勇毅有謀略,別的小孩所驚怕的,或不敢擔當的事,他都能泰然處理,所以從小就感覺他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長大後,張騫初時是在朝中當一名小小的郎官,算是漢武帝的侍從官,雖然他相貌堂堂,講起話來條理分明,但並沒有什麼特出的表現。
漢初對北方外患匈奴一向是以「和親」的政策來羈縻;然而漢武帝即位以後,這時的國力空前的雄厚,西漢王朝野進入了鼎盛時期,君主便想一雪和親屈辱之恥,極欲討伐匈奴。剛好這時朝廷從俘虜來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大月氏王想報殺父之仇,但苦於無人相助一事。武帝瞭解之後,便想要聯合大月氏共同來夾擊匈奴,以夷制夷,「斷匈右臂」,如此軍機事關要緊,此時必得盡快遣使聯絡西域各國才是。漢武帝於是立即下令徵募敢於承擔此一重任之才。
誥文一下,滿朝文武衡量此行出使的條件極為嚴苛,哪怕九死一生還不一定能覆旨歸來,於是眾卿皆低頷斂手,遲遲不諾。這時張騫就以他這樣一個小小郎官的職務,泰然挺身應募了,張騫不卑不亢、神色從容的說明瞭心意,自告奮勇的願肩負出使月氏的任務。武帝見他儀錶、談吐、識見、志節都非等閒,心下讚賞,便由此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於是張騫遂於建元二年(西元前一三九年),由一個叫堂邑甘父的胡籍奴隸作為響導,總共率領了一百多人,滿懷豪情的手持旌節,踏上了他這一生顛沛而傳奇的命運之路。
身在胡營心在漢 生死皆持漢家節
他們浩浩蕩蕩從長安出發,取道隴西(今甘肅東南部一帶),風塵僕僕、餐風露宿的備極艱辛,就在越過長城不久,不幸就被匈奴的騎兵發現了,結果被押送至匈奴王廷,張騫身上的使節仗以及給大月氏的印信、書函盡被搜走。匈奴王衡量再三,思慮既不能立斬漢使觸怒中土,更不能放鬆監禁縱虎歸山,只得先把張騫扣下了。他們對張騫實施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為籠絡、軟化張鶱,不由分說強行嫁給他一個匈奴女子作妻,並且在後來還生了兒子;一方面安排張騫行住舉止之處皆為眼線,毫無自由可言,就這樣子軟禁了他十年。
輾轉十年來,張騫居於匈奴王廷之中,他壯志未酬、人已中年、兒女漸長、豪情也不得不消磨了,只因他待人向來忠信寬厚,所以這段異居時間也很受當地人敬重,匈奴人都以為他已經以此為家了,連匈奴王也對他很好,一直希望張騫能為己所用。想不到這十年來的懷柔並沒有動搖過張鶱他一心一意要代朝廷、要為家國完成的通西域使命的決心,原來張騫一直還在等待著逃走的機會。十年後終於有一次,匈奴趁夜調動兵馬欲進攻邊陲,當夜張騫就趁機帶了十幾個人立即盜馬逃越大漠了,倉卒之際、死裡逃生,在日夜兼程、策馬狂奔之下,張騫終於離開了匈奴。
他們在沙漠裡奔了十多天了,又餓又渴又累,在極端忐忑無助之下,終於來到了大宛。想不到幸運的是,大宛國知道漢朝十分興盛,早就想與漢朝通使了,所以大宛便指派了嚮導和翻譯,將張騫一行一直送到了康居國去。而友善的康居國又從驛站將他們順利的轉送到大月氏。然而,這樣的好運並沒有延續,經過了這十幾年來的物換星移,最後他們抵達的大月氏已非原來的大月氏;他們靠著先前征服了大夏,已經定居在媯水一帶了,那裡地遼闊、水草肥、少侵擾、民安居,大月氏甘於臣服於匈奴,不思復仇之念,而且因為遠離漢朝,難知張騫所言虛實,所以無論張騫如何剖陳,終究還是不得要領呀!
因此可以說張鶱這十年來枕戈待旦的,以付出個人家庭生活甚至生命作為代價的,心心唸唸就是要「斷匈右臂」的目的,到此是完全落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願貿然回國的張鶱就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多,他利用這個流亡的機會,進一步的瞭解了匈奴的遷徙路線及水草分布,也瞭解了西域的情勢,也知道西域除大月氏外,尚有其他國家可以結盟。並且暗忖倘若日後還能有幸返國的話,必要建議漢朝向大宛購入良種汗血馬,以作重擊匈奴之用。

司馬遷最先於《史記》裡,稱張騫出使西域為「鑿空」。(網絡圖片)
就這樣,隨時不放棄希望但卻不得不拋妻棄子的張騫,就於元朔元年(西元前一二八年)決定啟程返國了,這一次的歸途,張鶱為避開匈奴控制地區,改從南道而返,他們翻過蔥嶺,沿崑崙山北麓而行,雖然取道刻意險峻,甚至還進入了羌人居住的地區,但最終還是被匈奴的騎兵俘獲了。再一次的,張騫一行難堪失望的回返匈奴王廷,再度被俘本應凶多吉少,幸好當時匈奴的單于已死,內部正為爭奪王位而一片混亂,拜此一時機所賜,匈奴只扣留了他一年多,尚未做出處置,張騫就因匈奴內亂而又再度乘機出逃了,這次張騫總算帶上了妻兒和甘父三人,於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返回了他朝思暮想的漢京故土。
真想不到經過了這一段前後十三年的流亡,當年離開長安後形容已變、風塵憔悴的張騫和甘父兩人,竟然還能隻身回朝;覆命之後,漢武帝慎重的聽取了他對西域的情況匯報,張騫並且詳細的提供了西域諸國的地理、物產、民情資料﹙而這些就是中國開國以來第一次熟悉西方之最早史料﹚;張騫所歷,令武帝滿朝盡皆感動,張騫所言,令天子文武同為震驚,遂在這位小郎官離開長安十三年後,武帝改任命他為太中大夫,拜堂邑甘父為奉使君了。
回看張鶱的這一趟歷程,足跡竟然遍及了天山南北和中亞、西亞各地,甚至晉朝人張華(西元232–300年)所著的《博物誌》中也提及張騫渡「西海」來到大秦,即指張騫曾渡今日地中海一事,張騫算是中原去西域諸國的史上第一人,雖然初始的軍事企圖並沒達到,但他卻開通了漢朝和西域的聯繫,所以此行後來被史家稱為「鑿空」之旅。司馬遷最先於《史記》裡,稱張騫出使西域為「鑿空」,譽其為首開中西交通之坦途。《中西交通史》亦云:「張騫出使西域,號曰鑿空,為中外關係史上空前大事」。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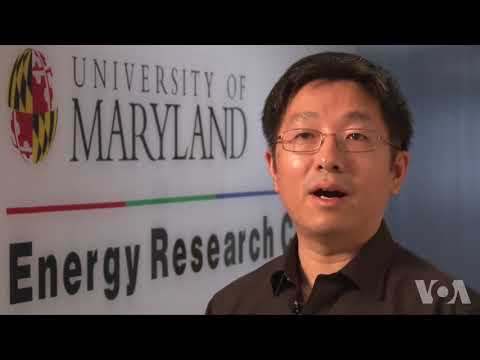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