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人们眼前马上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高山俊岭之上,两位风度翩翩的雅士席坐于苍岩飞瀑与古松巨石之间,一人举止优雅的抚琴,一人神态平和的侧耳静听;或在茂林修竹之间,一位身着宽袖长袍,气质刚毅洒脱的隐士,静坐于清泉碧溪畔临流抚琴,兴之所至,身心俱忘;或于苍松怪石之间,一位高士当风振衣,风致飘逸地行走在幽静的空山之中,身后的童子携带一张古琴,随同主人去访友寻知音。如此种种,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以弹琴抚弦为自娱,于安逸闲适中寻找清静高远心境的情态,曾在无数的诗词文赋与金石书画作品中得以尽情展现。最为人们熟知的是,被喻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琴棋书画”四大“雅好”中,古琴居于首位,此足见琴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难怪在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文人的形象总是有琴相伴。
那么,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乐器中,为什么惟独“琴”能够居众乐器中的“王者”地位,并被受历代文人青睐和推崇,从而成为他们常备不离的雅器呢?中国文人在古琴这件乐器中又寄寓了什么样的精神呢?
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秦始皇运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很快灭亡,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从此,懦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失意、不幸的命运,此时玄学盛行,遂使老庄之学得以广泛、深入地进入文士的精神世界。也因有了这种契机,使中国古代文人的儒、道互补的思维定势及心理模式结构开始正式成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道家崇尚自然的价值观、求退避的行为结构及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对儒家强调积极干预、进取有为及大一统的国家学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它恰恰又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对立和补充,并在思想方式上是彼此相通的。也就是说,儒道两家思想的转换,无需思想方式上推翻重来,只要相互转变,就可以在“达者兼济天下”与“隐者独善其身”之中便捷地作出人生路途的抉择。
于是,儒道两家在思想上的这种互补结构,为文人的二重人格提供了思想依据,如果得志时便是儒家,入世为官,乐观进取;一旦失意时便成为道家,出世隐居,消极退避;或者逃遁到比道家更与世无争的佛禅世界中去,从而构建起了中国古代文人“儒治世,道修身,释养心”的心理。正因为以老庄道家思想和佛禅的思想普遍渗入历代文人心田,同儒家思想共构互补地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入自觉的文化心理模式,完整意又上的中国古代文人也就因此形成了。
“中和”是儒家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解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表露时,叫做中;表情外露时,不偏于表现一种感情,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由此运行,万物生生不已。 “中”与“和”作为一对相关联的概念,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和”是把许多复杂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中”则是指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中和”的主张就是将矛盾的各方面调和统一起来,使其和谐适度,从而达到最佳状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音乐观念和审美情趣便有了高下雅俗之分。虽然士人在音乐审美观念上各不相同,但都在推崇“雅”的观念上趋于一致。儒家所推崇的“雅乐”,要求合乎礼的规范,是那种使“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以平德和”(《左传》)的宫廷祭典音乐。这种用于典礼音乐的演奏,节奏缓和,声调平淡,造成庄严、肃穆、平静、和谐、安详的气氛,给人以中庸平和的音乐美感,能使人从中得到伦理道德的感化。相对“雅乐”而言,儒家则对代表民间俗乐的“郑卫之音”大加批驳与贬抵。在儒家的观念中,春秋时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放荡悦耳,这种靡靡之音能消磨人们的意志,使人贪图享乐,颓废堕落,所以后世以“郑卫之音”代表放荡激越的音乐。因此,音乐中的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均发自人心,听其音声,就可知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其间体现演奏者雅俗志趣的音乐自然也清晰可辨。
对于儒家所推崇的“雅乐”,道家却以表现人的自然情性为美的音乐审美观。这种音乐审美观尊崇自然、无为、朴素、恬淡的特点,即在体现人纯朴的本性音乐中,助益于人“纯粹而不杂,静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 ( 《庄子•刻意》)的养生之道,亦即是老子所讲的“致虚极,守静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才奉“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无声音乐为音乐美的极致。至此,道家在儒家所赋予的政治功利和社会伦理意义的“雅俗”音乐观之外,客观上又提出了一种纯粹以音乐审美情趣和品位来划分,由典雅精致、虚静简淡为特征的又一重“雅”乐的审美观念。这种“虚静简淡”的意趣的萌生,对后来的文人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儒、道互补思想的具体显现,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定势和人格模式一样,“正中平和”和“静淡远虚”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音乐观,共同构成了文人音乐的审美基础。这种代表着文人音乐审美精神与美学取向,又在的古琴艺术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琴”在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不仅创造并完善了独特的琴器、琴曲、琴谱等,更因其深沉高雅的音色品质与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及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古人对琴的评价极高,西汉时期便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魏晋名士嵇康在其《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人顾况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另外,随着“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的修身养性功能被文人日益强调,“左琴右书”、“士大夫无故不撤琴瑟”等古琴音乐观念在凝固,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可替代。琴成为历代文人们具备音乐修养及实践技能必修的一种乐器,同时也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情操的最佳体现方式。毫无疑问,琴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古琴的神奇魅力,首先来自于琴器所特有的音色品质,而这些特有的音色效果又与琴的材质、形制、结构、髹漆等斫制工艺有着直接的关系。琴体的构成,主要是由一整块木材腹腔开剜后制作的面板与底板胶合,内部形成一个狭长的“共鸣箱”,然后再周身髹以厚厚的大漆而成。弹拨类的弦鸣乐器,是以弹拨极具张力的弦为振动源,再与由面板和底板结合构成的共鸣体产生共振而发音的。琴的弦位较长,音量不大但余韵悠长,面、底板浑厚且共鸣箱体积较小,特别是通体表层髹有厚厚的漆胎,这样特殊的斫制与构造方式,使共鸣体振动不充分且有传播阻碍,造成琴在发音上具有轻微淡雅、深沉悠远,圆润古厚的音色特点。而这些发音特点,恰与历代文人在音乐上追求的“中正平和”、“温良敦厚”及“虚静简淡”的审美情趣相合。可以说,古琴特殊的斫制方式决定了演奏者崇“和”尚“雅”的审美趣尚,而历代文人对古琴的推崇与偏爱,又促进了古琴形制的不断发展和音乐表现力的逐步完善,其特有的音色品质与后来日益丰富的其他乐器品种及民间俗乐越来越不相容,琴逐渐成为了文人雅士们抒发高雅情怀所专用的乐器。
相对来说,古琴的音量不大,但古琴主要是古代文人在书房中自娱或在三、五好友间欣赏交流,在古人眼中:“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古琴的声音大小正好适中,体现了“中和”之美。
就总体而言,古琴的音色有散音、按音与泛音三大类型。散音,指左手不按弦,以右手弹弦所发出的空弦音。散音即空弦音,其特点是比较浑厚宏亮,共鸣性强,余音悠长。按音,指右手弹弦,左手指顺弦依征位按弦所发出的声音为按音。按音没有散音清亮,共鸣性和余音亦相对较弱,但其音温厚、结实,其多变的走手指法通过改变琴弦的不同张力,创造出无穷的音色旋律,古琴音乐的主旋律也主要是由按音来表现的。泛音,为右手弹弦,左指对准征位轻点琴弦,得音清亮空灵,称为泛音。泛音则清脆,晶莹、纯净、明亮,有金属声,富于弹性,与散音的厚重深沉、按音的沉着多变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古琴还分为低音区、中音区与高音区三个不同的发音部位,低音区低沉、浑厚、古朴、苍老,余音绵长不绝,高音区则清亮圆润,富有穿透力度而又具醇厚之韵。中音区取音“中和”。在琴曲中,这些充满矛盾的不同种音色常常配合使用,通过高妙的处理手法,使古琴的散音、按音、泛音及高、中、低音区调和在同一首曲中,使丰富的音色得以和谐统一。这恰与中国文人崇“和”的观念相契合。
相对文人古琴艺术所奉的“正中平和”的审美理想是为导向儒家人格为宗旨,那么,他们在实际操琴中所取的“静淡远虚”的审美情趣以及创造艺术意境的美学要求,则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古琴是一门音乐艺术,这里的“静”,只是要求操琴者在弹奏时的精神状态,弹奏中操琴者需心无杂念,心神贯注,这样才能把握住音乐的内涵及发展脉络,进入“未曾成曲先有情”的境界中,这样在演奏中才能达到与“闹”相对的“急而不乱,多而不繁”的“静”境。“淡”是以“静”为前提而生发出的古琴弹奏中情绪的处理。宋代周敦颐曾说:“乐声淡,则听心平”,心境的平和来自于淡泊的琴声,“淡”的意境谋求的是一种超尘脱俗、自甘淡泊的傲我情境,孤芳自赏的趣味,是一种含蓄的美。由“淡”而给古琴音乐带来含蓄之美,实际上给操琴者带来了更多的主观联想的“远”的余地。徐上瀛对“远”的诠释说:“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古琴的减字谱,没有明显的节拍及节奏标记,乐谱只是记录作曲者情感体验的音符体系,演奏者对谱演奏难免会对原曲精神进行追寻、领略、探索的问题。在体会的过程中,演奏者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身的思想情感体验来对作品进行相应的解释,正是演奏者在演奏处理进行中的再创造,使演奏者在乐曲中掺入自我联想,演释乐曲的内涵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天地。通过“远”的主观体验与客观对象的交融互渗,达到了道家所谓的“得意而忘形”,原乐曲此时仅是一具徒有形式的空框,其中洋溢着的纯粹是演奏者个人丰富而细腻、广阔而微妙的心理体验。而“虚”则是“淡”与“远”这两者的升华,又是对它们的否定,是琴艺中达到“无我”,神游气化自失于自然的极境。嵇康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诗句,其音有尽而意无穷,声有竭而情无限,演奏者进入的是与自然浑然一体、元比广阔、深邃的审美境界。“虚”是文人们在琴艺中追求的最高境界。
文人音乐常以“正中平和”与“静淡远虚”相提并论,但在实际支配和指导着文人音乐活动的审美意识,归根结底是“静淡远虚”。虽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道互补思想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定势和人格模式,但文人处于各自不同的时空环境,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及其生活方式也相应而异。当文人得志入世之时,以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忙的是忧国忧君,讲的是礼乐文章,基本无暇顾及琴棋书画的个体活动。可是在文人仕途失意之际,消极退隐之后,又常引道家思想为安慰,由“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的琴棋书画,达到修身养心的目的。因此,这种“静淡远虚”的道家思想直接影响古琴、书画等艺术创作的审美趣味。
审美思想决定演奏风格、环境及琴曲题材的选择。古琴乐器的琴弦长震动缓慢,传统琴人一般都使用丝弦,丝弦音色温润醇厚,加上琴身的木板及厚厚的漆胎覆盖,致使古琴音量相对微弱低沉。特殊的构造与音色决定琴不适宜于弹太快速及喧闹的乐曲,而一些舒缓淡雅的曲子则更宜于弹奏。相对那些被认为有“杀气”或“燥急”的琴曲,文人们更欣赏表现山水、隐逸题材的琴曲作品。中国文人入世时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讲究节操品性,选择梅花、幽兰、仙鹤等题材的琴曲来体现自己的高洁情操;避世时则以道家为主,讲究脱俗自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富有正义感,刚正不阿的、怀着忧国忧民之远大抱负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往往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而不幸。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文人们就退隐山林,以“琴棋书画”自娱来排解精神上的孤独与寂寞。逐渐,文人们形成了一种平和冲淡,超然脱俗,不拘形迹,不羡富贵,不重荣辱,随遇而安,一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处事风格,从而实现并达到“穷则独善其身”的超脱境界。
因此,文人琴家创作了大量描写山水、隐逸内容的琴曲,如《高山》、《流水》、《石上流泉》、《潇湘水云》、《泛沧浪》、《平沙落雁》、《秋江夜泊》、《遁世操》、《招隐》、《山居吟》、《泛沧浪》、《归去来辞》、《渔樵问答》、《渔歌》、《樵歌》等等。从这些琴曲所表现的意境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思想脉搏与深邃的内在精神。
另外,古琴因弦位长,在琴面上按弦上下弹奏丰富走手音时,音量总是呈现出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弱化”和“渐微”的趋势。这样断而复续的演奏方式造成发音疏淡空灵、若有若无的效果,使琴乐的演奏具有虚灵、悠远、飘渺的意境,这也正是琴乐的高妙之处。琴乐弹奏的特殊手法与效果,特别要求演奏者对环境的选择与心境的营造。古人十分重视环境的选择,明代琴家杨表正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观宇中;值二气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静室,坐定,心不外驰,飞血和平,方与神合,灵与道合。”古人弹琴时对环境的要求还有许多规矩与各种禁忌,例如“五不弹”、“八不弹”、“沐浴”、“宽衣”、“焚香”等等。这些看似繁杂的内容,其实最后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在弹奏时得到一种自由、洒脱的心境与风度。
《大学》开篇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古代想在天下显明高尚品德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的人,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想要提高自身修养的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反之,只要心志端正,才能使自身具有修养;自身有修养,然后家庭才能整治好;家庭整治好,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然后才能平定天下。因此,“正心”是历代文人实现一切崇高理想最重要的基础。
怎么样才能端正自己的心态呢?因《琴操》中有:“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的说法,所以历代人们都延续这种观点,认为琴的创制,就是为修身“正心”的。汉代时文人明确提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唐代司马承桢《素琴传》:“琴者禁也,以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志,修身理性,返其天真。”明代高濂在论琴时所说:“故音之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发乎人心,而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听子音声,可先知也,岂他乐云乎?”高濂论琴,阐述的中心论点是:“知琴者,以雅音为正。”要达到如此境界,不仅体现在技法的规范上,还体现在弹琴者的心志与学问上。“正中平和”是文人音乐的审美理想,而其中的“正”,又是理想化的文人合乎儒道人格修养的标准。汉代刘向《说苑》中所载的孔子对子路弹琴的要求是“和节中正”、“温严恭庄”。清代琴人祝凤喈也曾说“鼓琴曲而至神化,要在于养心。养心为一身之主。语言举动,悉由所发而应之。心正,则言行亦正;邪,则亦邪,此人学之犬端也。”这些要求与其说是一种琴乐的审美,倒不如说是文人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规范。弹琴的目的就是要求在抚琴过程中达到扶正祛邪、陶冶性情的效果,使文人在弹琴的过程中得到趋于完美的人格修养。
如此诸多言论,都是阐明琴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乐器本身,不仅能够正心、修身,而且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能,这些都需要琴的纯正声音作为资助。琴因其特有的音色品质与文化内涵,被历代文人们尊崇为修身养性的“雅器”,音乐中体现的是高雅的胸襟、学识与修养,也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情操的最佳体现方式。因此,琴乐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被历代文化精英们不断丰富完善,使古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远超于一般其他乐器,古琴成为最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与文人精神的民族乐器。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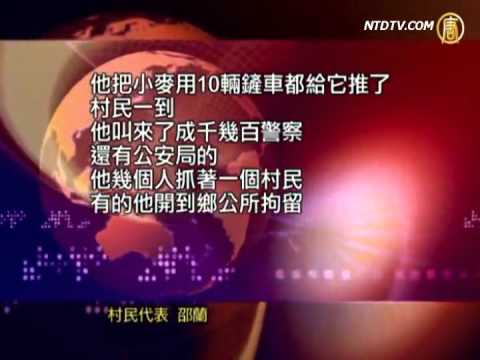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