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序曲:风中的红焰
——那是燃烧的虚无,那是哲人丢失的心
芸芸众生终生渴慕世俗的幸福,最终却被空洞的死亡嘲弄;哲人以追求真理为天职,尽管在真理与死亡的对视中,许多哲人最终只看到了永恒的困惑。金圣悲,一位从雷电撕裂的苍穹走入尘世的哲人,此次重返西藏高原,却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要寻找他丢失在高原上的心。
荒凉的寂寞陪伴他,青铜色的风引导他,经过万里跋涉,终于来到心丢失的地方。那正是玛旁雍错湖旁的草原。五年前,金圣悲怀着让心净洁的愿望走上雪域高原。长久生活在汉人中,犹如沙尘暴一样遮天蔽日的庸俗之气,使哲人高傲的心蒙上了重重灰尘。那种心变得肮脏的感觉比猥琐的死更可怕——心都令人厌恶,生命中还有什么值得珍视。于是,金圣悲来到西藏高原,这离生命的圣火太阳最近的地方。他希望高原上能烧裂岩石的阳光,为他洗去心上的灰尘;他愿让心沐浴在尘世之外的净洁中。
就在那次净化心的旅程中,恋情像苍天降下的迅急的泪雨,在金圣悲坚硬的心上,撞击成一片迷茫的紫雾。五年过去了,那位藏族少女仍然在向他凝视;金圣悲知道,即使时间都因为衰老而死去,少女的凝视也不会消失。在命运的偶然性造成的最初凝视中,金圣悲从少女的眼睛里看到了动荡的风吹乱百花的神韵,而哲人的心立刻沉迷于那比真理更醉人的意境深处;在离别前的最后一夜,少女为哲人彻夜吟唱,满天璀璨的星群,也不如少女眼睛里的泪影晶莹;哲人为少女而纵酒,他的心像一块烧成深红的顽石,感觉著炽烈而坚硬的疼痛。
分别在黎明中。一夜未眠,少女的眼睛现出几缕纤秀妖娆的血丝,仿佛雪雾迷茫的天空中那嫣红的流云。哲人与少女对视著,就像永恒和无限在诀别。终于,金圣悲开始倒退而行,走向辽远的地平线——他要在同少女的对视中离去。也许为了挽留哲人,无情的石块一次又一次绊倒哲人倒退而行的足步,可是,又有谁能留住荒野的风。
直到少女的身姿被地平线遮住,哲人才把背影转向美人,他知道少女定然还在地平线之下向他凝注。然而,就在背影转向美人的瞬间,金圣悲骤然感到他的心由于过分炽烈而化为灰烬,在浅紫色的高原之风中飘散;他的心丢失了,原来心跳荡的地方,只有一团死寂而黑暗的空虚在抽搐。
即使承受心丢失的恐怖感也要离去,不是由于他的生命经历太多时间风雨的侵蚀已经如同一块破裂的岩石,而少女的生命则像刚消融的雪水河一样晶蓝明澈,因为,哲人或者诗者不会记住自己的年纪,他们是超越时间的存在。金圣悲与少女诀别,只在于一个理由:属于少女的恋情是一种至美,圣洁灿烂得犹如高山之巅流溢着金色阳光的白雪,而至美的恋情需要高贵的男人将其当作终生不渝的情感事业来对待,那是诗的事业,可是,哲人却不得不以真理为天职,他不能背弃真理的事业。
当代汉人不仅丧失民族文化之魂,而且心灵腐烂于物欲;在这个群体中寻找真理,只意味着精神的苦役,在心丢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尽管又经历了五年的精神苦役,真理依然遥远如永远也走不到的地平线。于是,失望达于极致之时,金圣悲突然清醒地意识到,美才是真理的王冠和生命意义的极致;那位藏族少女圣洁而自然的生命之美,才是真理的万王之王——他的心失落在真理之巅。
这次,正是为找回失落的心,金圣悲又追随记忆的脚步,来到五年前他与藏族少女相遇的地方。然而,那座帐幕却不见了,只有血锈色和骨灰色的草,向哲人表述荒凉的悲情。
少女原来和她的祖母住在一起。祖母的丈夫是一位康巴铁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参加藏民大起义,与中共军队作浴血之战。血战失败后,他就消失了,像一片曾经覆蓋铁褐色大地的深红晚霞消失在暗夜中。奶奶多方打听丈夫的踪迹,却一直没有下落。她相信,那个雄豹一样壮烈的男人,定然已经战死在翻越喜马拉雅的流亡之路上——那本就是一条红血和白骨铺成的路。半个世纪以来,祖母一直作一件事:每年都用几个月时间,牵着牦牛,追寻西藏人流亡的道路,去捡拾战死的藏人的骨头,装到牦牛毛编织成的袋中,驼在牦牛背上,运回来。然后,在白骨上刻出经文,堆在高岗之上。一年剩下的时间,奶奶便到岗仁波钦圣山去转山,为死在流亡路上的丈夫和别的藏人祈祷。她盼望高原上不停的风早些把白骨吹成尘雾,或者夏日的雷电将白骨殛碎;她相信,只有白骨灰飞烟灭,战死者的灵魂才能超渡。
半个世纪过去,连岩石也会苍老很多。祖母由花枝般的少妇变成身形佝偻的老妇人。可是,她生命的逻辑像日出日落一样,在同一件事情中循环。她甚至比太阳更守信,因为,日出日落有时也会被乌云遮蔽,而她的生命逻辑从不会中断。
然而,狂风能吹裂岩石,却吹不碎白骨;雷电常劈殛大地,却似乎不敢击中那刻着经文的白骨之堆。五年前,金圣悲见到她时,从她的眼睛里只看到铁锈色的迷茫。“也许,怀恋之情到极致之处,便是一片铁铸的迷茫——迷茫,但坚硬著。”当时,金圣悲如是想。
此刻,发现少女和祖母住过的帐幕以及她们的羊群消失了,金圣悲就意识到,时间在又一次证明它的冷酷,即时间比生命更坚硬。不过,时间却不明白,失去属于心灵的生命,时间就像没有字迹的稿纸一样没有意义。一位路过的牧民告诉金圣悲,老婆婆已经死去四年多;小女孩作了尼姑。
金圣悲决定去寻找那座死于流亡之路的藏人白骨筑成的玛尼堆。那是一位坚韧的妇女半个世纪的生命遗迹。而一个丢失了心的哲人,似乎也只能把走向枯骨,作为最终的命运之路。
玛旁雍错湖就像从大地深处渗出的对苍天的恋情:辽阔、宁静而蔚蓝。湖的西北方,岗仁波钦峰下部高峻的悬崖犹如烧成暗红的铁铸的底座,雄浑的峰顶呈现出弧形,像白雪覆蓋的古老日球的遗骸被铁铸的底座托向尘世之外——圣山的形象似乎隐喻著关于时间起始之前和日球熄灭之后的哲理。湖的南方,纳木那尼峰白得发蓝,仿佛从天空深远处浮现出的英雄史诗的轮廓。
踏着湖边贴地生长的枯红的草甸,金圣悲向纳木那尼峰的方向走去。或许因为正走向那堆英勇的藏人的白骨,哲人的脚步变得缓慢而庄重。一条狭长的蓝紫色阴云凝结在雪峰的中间,飞舞闪耀的雷电将哲人的眼睛擦拭得格外明亮。
雪线以下,一道道山脊如同重重铁黑色的波涛,涌向莹白胜玉的纳木那尼峰。在一座仿佛铁铸的高崖上,现出流亡藏人的枯骨筑成的玛尼堆。灰蓝色的风把一位女子的梵唱,从枯骨的玛尼堆旁送进金圣悲生命的深处。
“呵——,那是梅朵… … 。”金圣悲低声对自己说;他毫无疑义地辨认出梵唱声属于使他的心丢失的少女。尽管五年前少女为他吟唱的是生命与爱情之歌,此刻的梵唱是为枯骨祈祷,但是,音韵的生命风格却没有改变:那深情的声音令人相信心灵的存在,因为,声音似乎是从比天际更遥远的地方飘来——除了心灵,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天际更深远?
金圣悲快步走上一道山脊;枯骨的玛尼堆后面,一位女僧人出现在他视野中。宽大的绛红色僧衣下,美女身形的俊秀神韵依然动人魂魄。就在金圣悲即将像骤起的狂风冲向前去的瞬间,他的脚步却被无形的铁链拴住:他知道,如果冲过去,如痴如狂的思恋会让他把少女紧搂在胸前。但是,他又怎么能亵渎一位正为枯骨祈祷的女僧人。
旁边,一堆形态峻峭的破裂岩石仿佛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岩石血锈般的色彩吸引了金圣悲。他跃上岩石堆,在最高处坐下。长久在高原上漫游,太阳已经为他的面容镀上一层青铜色。那正是属于男人的最美的色泽。此刻,哲人就像一只青铜铸成的消瘦的鹰,蹲踞在浴血的岩石上沉思。金圣悲决定,等夜色降临之后,再走近梅朵。哲人觉得,当黑暗遮住梅朵兰花般的眼睛和美丽的容颜时,他才能宁静地向少女倾诉思恋的激情和哲理,倾诉心丢失后的苦痛——倾诉,是为了找回他的心。
时间又一次把日球埋葬在虚无中,苍穹和大地都呈现出坚硬的铁黑色。然而,从地平线下斜射上来的阳光,却把纳木那尼雪峰辉映得金碧辉煌,宛似金色和紫色的晚霞栖息的圣殿。雪峰下面,阴云呈现出凶险的暗红色,银蛇般的雷电在阴云间闪烁明灭,回响千里的雷声就像雄烈的鬼魂在纵酒狂啸。远方,岗仁波钦峰犹如金色灿烂的命运之轮,在铁黑色的苍天和大地间滚动。
黑色高崖上,枯骨的玛尼堆从阳光的余辉中呈现出来,像银火焰般艶丽;刻在白骨上的形态优美的经文都涂成土红色或者墨蓝色,这使那堆历经半个世纪风霜雪雨的枯骨,看起来酷似属于死亡的艺术品。梅朵的梵唱像无尽的柔情,轻抚美丽的白骨;她绛红色的僧衣随着呼啸的风翻飞飘舞——那是激情动荡的召唤。
来自无极之处的预感突如其来崛起在金圣悲丢失了心的胸膛里;天地之间覆蓋著时间枯死之后的寂静。低垂的阴云被雷电烧成炽烈的蓝白色,随后,一团雷火犹如炫目的天启,从阴云中飞降而下,殛中了枯骨的玛尼堆。铁黑的高崖上腾起一片灿烂的光辉,枯骨破碎为银色的雪雾,梅朵的僧衣化作心形的火焰,在紫色的风中翩翩起舞。火焰殷红得犹如燃烧的少女之血;梅朵的梵唱声仍然从火焰中传出,只是吟唱失去了佛意的宁静,却获得了火焰的炽烈。
“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冲上前去,我为什么犹豫——我因此永远失去与梅朵对视的机会,我再不可能向她倾诉我的思恋… … 。”当雷电之火将枯骨殛为尘雾并点燃梅朵的那一刻,金圣悲痛悔地想。同时哲人意识到,这种痛悔之情将成为他骨头上终生不愈的伤痕。
火焰的拥抱中,梅朵的形态辉煌而生机盎然,像雷电在哲人眼睛上刻出的一座正在起舞的菩萨雕像。从淡紫色风中,金圣悲呼吸到迷人的芳香。理智几乎本能地告诉他,芳香是由于梅朵的僧衣薰过龙涎香。但是,金圣悲却对清醒的理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他厌恶那种不给诗意和美留下一丝余地的聪慧。哲人坚信,风中的芳香来自美人被烈焰焚烧的身体;那芳香是梅朵的白骨的氲氤。少女的骨香缭绕之中,金圣悲获得了一个启示:只有超越纯粹的理性,才能进入真正的哲学意境——真正的哲学只属于血肉丰饶的生命之美。
一声拖长的悽厉的悲呼把铁黑色的天幕都划伤了,阴云被苍天的血染成深红。焚身的苦痛使梅朵妖娆的身体炽烈地婉转扭动,仿佛在心形的红焰中作情欲之舞。金圣悲呼啸著从岩石堆上跃下,向燃烧的梅朵奔去。他繁富的生命净化为一个清澈的愿望——把那团风中的红焰搂在胸前。
金圣悲刚奔上枯黑的断崖,龙卷风便如神迹般从崖顶上腾空而起;枯骨苍白的尘雾同那团殷红的火焰一起,随飞旋呼啸的暗紫色风柱,迅速地升向高空。在那里,铁黑色的苍天深处,纳木那尼雪峰依然像一个金色的召唤在闪耀。
一切都消失为黑暗的虚无。金圣悲颓然仆倒,想投入死亡的深渊。但是,他的胸腔紧贴住的只是坚硬的绝望。他悲哀地想:“难道连死亡也拒绝我,一个丢失了心的人。”就在这时,金圣悲却骤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心的疼痛,疼得他几乎要用牙齿咬碎顽石。
“是的,梅朵把心还给了我——那风中的红焰就是我的心,她红焰中的舞姿就是给我的遗嘱。可是,遗嘱意味着什么?…. … 噢,火焰原来也会疼痛,而且疼得如此炽烈… … 怀着一颗火焰的心,还有焚心的痛苦,我今后的命运将走向何方?”金圣悲的思绪随荒野之风飘荡;他的目光直视峭立的黑暗,在漫漫长夜中等待命运的启示。
苍白的黎明时分,一个宿命的启示,像闪著寒光的冰针刺入金圣悲青铜色的眼睛。在炫目的失明感中,哲人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命责任:“走遍天涯海角;上穷苍天,下穷九地,去寻找藏人的灵魂,并把那华美的灵魂安放在时代精神之巅——这是梅朵烈焰中的舞姿给我的遗嘱。只有完成了这个遗嘱,我的心,那风中的红焰才会熄灭:那属于火焰之心的疼痛,才会化为灿烂的虚无。噢,风中的红焰,本就是燃烧的虚无。… … 让我开始走上寻找藏人灵魂的旅程吧,时代精神之巅已经荒凉得太久了。寻找,就从红血和白骨铺成的藏人流亡之路开始——那翻越喜马拉雅的心灵之路。”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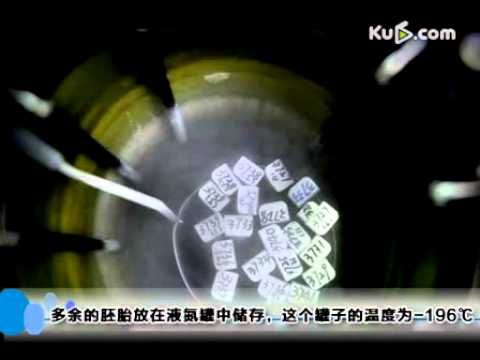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