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縣委召集各鄉鎮書記會議核實產量,把產量問題上綱到擁護總路線還是反對總路線,批評有的黨員「離右派只有50米」。
東陳鄉鄉長賀正瀾先報畝產670斤,聲明根據鄉幹部試驗田推算。此公原是縣供銷社副主任,曾與我同事,性格內向,溫文爾雅,說話慢吞吞,不會吹牛,林海鄉不甘落後,報700斤,丹城鎮報750斤,半路跳出農業無名小卒以漁業為主的爵溪鎮報800斤,超過丹城鎮。丹城鎮委書記坐不住了,起身到縣農業科辦公室一轉,就向主持會議的縣委副書記王化祥說,上午鎮裡全面清倉核產,畝產量增加到860斤。
這樣的你追我趕,還不能使縣裡滿意,要求回去再進行一次認真核產。但核來核去不如人意。縣委決定以搞運動方式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反瞞產」鬥爭,區為單位集中合作社支部書記辦學習班。
南莊區學習班,放在區委叫「小東洋」的一座大房子裡,集中農業社書記和黨員共60餘人。大查合作社與生產小隊的瞞產行為,採取人人過關辦法,對思想不通者小會幫,大會促。
東陳鄉馬崗支部書記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癩頭」,思想不通,被宣布「隔離反省」,關押起來,該鄉一名黨員被開除黨籍。強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堅持,乖乖地在黨委確定的產量表上簽字,南莊區早稻一季畝產上了800斤,為以後高徵購埋下伏筆。
接下來浮誇之風借「拔白旗」「插紅旗」越刮越猛。何謂「拔白旗」?誰要是對大躍進高指標懷疑就組織上採取措施,撤職。而誰能跟著浮誇的,提拔到領導崗位,叫「插紅旗」。
廣播、報紙天天宣傳「一天等於20年」。科學家錢學森在6月16日《中國青年報》撰文稱:「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畝田上的太陽光能30%,稻麥畝產量就可達到4萬斤。」接著6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河北安國南婁底鄉卓頭村畝小麥畝產5100斤,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
《人民日報》又報導:湖北麻城溪河鄉第一農業社早稻畝產36960斤。一時丹城街頭「學麻城、趕麻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標語鋪天蓋地,全縣召開四級幹部大會號召「實現畝產噸糧縣」《人民日報》又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一塊試驗田稻穀畝產130434斤10兩4錢,更離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廣東番禺縣訪問記》說他親眼看到了這個縣畝產蕃薯100萬斤、水稻畝產5萬斤。糧管所每年要收購蕃薯運往城市供應居民,一個麻袋只能裝90至100斤,100萬斤就得裝1萬餘袋,若堆到一畝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層樓那麼高。
學習時我說過不可信的話,當時大家和我一樣認為是吹牛,不料以後因此惹禍,此為後話。
《人民日報》不斷發表社論,大批「條件論」,鼓吹「人定勝天」,繼續為浮誇風推波助瀾,縣委要求各區、鄉書記挂帥「移苗並丘」放衛星,即把別處同一品種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塊施有大量基肥的田裡,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說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陽能多株多穗出高產」。不許社員反對,強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並丘」,大片本來長勢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塊田,釘上木牌,寫上××衛星田。
像山縣委的衛星田在南莊白鶴廟農場,移苗完成後,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著一位小姑娘以示這塊稻子產量之高,照片向各新聞單位發出,記者是朱華庭,後來老朱說「下面放了凳」。其餘各鄉的衛星田,都照縣委的樣子。由於植株密不透風,莖葉發黃,發動眾多女社員,手執芭蕉扇「扇苗通風」,終因違反事物客觀規律而受懲罰,全部腐爛,顆粒無收。
明明已經勞民傷財,雞飛蛋打,還要猛吹牛皮。大徐區農業書記樊敬道的「衛星田」,在沒有腐爛時,報了畝產2000斤。縣裡王副書記就說,你的名字就是「萬斤稻」(樊敬道諧音),就報1萬斤吧。像山最大的一顆衛星是牆頭區委書記葉樹春的畝產16萬斤。
在大躍進大浮誇的凱歌聲裡,10月1日像山全縣農民敲鑼打鼓迎來了全面公社化,38個鄉鎮全部撤銷,從南到北劃分為9個公社。丹城鎮、爵溪鎮、南莊區,加上大徐、牆頭等4個鄉,組成全縣最大的像山人民公社,後改稱丹城公社,共12個管理區,108個農業合作社改稱為生產大隊,2.8萬戶,8.6萬餘人,9萬餘畝土地,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結合。
10月4日寧海象山兩縣合併,撤消寧海縣,稱像山縣。縣治從丹城遷往寧城,公社辦公先在孔聖殿,半年後遷至城隍廟孤兒院(今縣黨校),糧管所並入丹城公社稱公社糧油部(對上仍稱糧管所),辦公在青草巷。我被宣布任糧油部副主任,公社書記董方祥(縣委常委),另有三名副書記分管農業、商業、副業。
主任牟洪緒不久調任縣工業局,我的老同事賀正瀾為公社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黨委委員。取消自留地,不准個人養家禽、家畜,為防止社員私自宰殺吃掉或到市上出售,大隊派出專門捕雞隊拿著網具挨戶捕捉(公社成立牧場),以生產大隊為單位辦起公共食堂,所有用具除一部分新添,到各社員家裡拿。
各戶的灶頭大部被扒掉,拆下磚石給食堂壘灶,米甏水缸都集中到食堂。社員家裡的口糧、種子歸大隊倉庫。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軍事化,小隊是排,大隊稱連,管理區叫營,公社為團。取消按勞分配,實行八個不要錢,即吃飯不要錢,吃菜不要錢,理髮不要錢,穿草鞋不要錢,孩子讀書不要錢,婦女分娩進產院不要錢,到縫紉組補破衣不要錢,老人死亡棺材不要錢。各生產大隊男女社員由公社統一發工資,正勞力每月8元,半勞力每月4元(只發2個月,公社財政不支,停發)。
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勞動力、資金、生產資料與物資,公社有權「平調」(通稱一平二調),如爵溪管理區漁隊到像山港養殖海帶,需用大量木材、毛竹,憑公社一紙通知,可從沿港的牆頭、亭溪兩管理區隨意砍伐、取用,甚至幾百個養海帶社員睡的鋪板也向社員家裡取用,有的還把人家壽材板也拿來了,真是到了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
每個食堂選派成分好的人擔任炊事工作,大隊書記挂帥。食堂與食堂之間開始競賽,集中農村做點心好手,保證食堂餐餐有紅豆團、年糕、湯果吃,公社常召開現場會,互相觀摹,比誰家食堂飯香菜美花樣多。社員們在這股共產風裹挾下,也確實興奮異常。生產有領導,吃飯在食堂,工資發現鈔,真以為到了共產主義。
但是幾千年小農經濟私心一時難改,「一大二公」與我關係不大,出現干農活偷懶粗放,出門一條龍,每人只背一把鋤,集體的犁、耙沒有人拿,推來推去得由小隊長一人背。「人頭不到齊,鋤頭拄肚皮」,聽到食堂鐘聲,馬上放下農活,成了一群蜂。
那麼放開肚皮吃飽飯又是如何呢?據說長街公社有一社員因吃了太多的糯米飯撐死了,我沒親眼看到。但一次在南莊管理區洋心大隊食堂,嚴重浪費卻是親眼所見,已是下午兩點鐘,還有幾十個社員在天井裡亂哄哄等飯吃。支部書記王德明是個癩子,頭上無毛,卻淌著黃豆大汗珠,正在從大鍋裡把糯米飯扒到一隻大木桶裡去,頭上的汗珠雨滴似的滴進了飯桶,對我抱怨說:「這些人真不識相,今天吃糯米飯,第一批人吃飽了,後來的人還未飽,再煮。等後來的人吃飽了,先吃的人又喊沒飽了,於是又煮,一直煮到現在。」我說已經兩點多鐘,一直煮到吃晚飯吧!下午不出工了?令他恍然大悟,大吼一聲,不煮了!才攆走一些胡鬧的人。
公社還印製了可在全社108個大隊食堂通用的「流動飯票」,由各生產大隊統一領取,供社員公出等使用,每逢丹城市集,四面八方的社員大家先去東、南、西、北門各大隊食堂巡視一遍,哪一家食堂飯菜好,就一齊擁向這個食堂就餐,把飯菜一掃而光,為此經常有人打架。作為基層糧食工作者,肩負著統購統銷,保證「軍需民食」和安排社員生活雙重責任。糧食是寶中之寶,面對浪費憂心如焚。據我們掌握的生產隊完成徵購指標後留下的口糧實際庫存不足半年,經不起如此浪費。
在一次縣糧食局召開各公社糧管所長會議上,我說了食堂浪費糧食和某些社員吃飯比賽等不良現象,被財貿部某領導斥為「懷疑人民公社優越性」。糧食浪費不僅表現在消費,還表現在收穫方面:1958年下半年,忽然傳達中共中央要「三年超英、七年趕美」,全民煉鐵,大搞「小土群」,像山城鄉大街小巷、學校操場、菜市場、生產隊晒場都是用磚頭壘起來的小高爐,到處是亂哄哄的滿臉塵灰煙火色的人群,我也被指定擔任一座小高爐爐長,五天五夜不合眼,煉不出一點鐵。公社要求每個生產隊白天黑夜地幹,但就是不出鐵,命令社員把家裡廢鐵都上交,人人上山找礦石,砍伐樹木,誰不服從就是反革命。
報紙上說全國6億人口,投入大煉鋼鐵勞動力超過1億,丹城公社當時號稱3萬人上陣。時值秋收,勞動力不夠用,命令開夜工。被「小高爐」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員,把玻璃小方燈掛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睡覺,管理區幹部登樓瞭望,田畈上燈光閃爍,以為都在勞動,結果有很多稻子和蕃薯爛在地裡,有的甚至堆在路邊沒挑回來任其腐爛。有一首民謠:「日夜小高爐,山上樹斫完,田裡稻爛完,家裡鍋砸完。」丹城公社8萬餘人,在身不由己的大浮誇共產風裡度過了1958年。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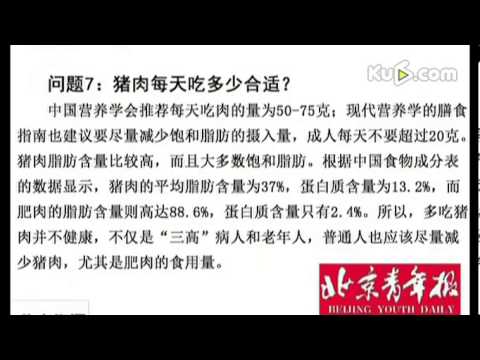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