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九年,對中共黑幫屬下的御用工具---作協來說,是驚喜之餘又魂遊了一回地獄,之後才又迴光返照吊著那口氣。所謂驚喜,是指增添了金庸這樣一個大頭蘿蔔;魂遊地獄,是北京著名作家鄭淵潔的退出和一批八零後作家們對它的嘲弄與不稀罕。試想,連韓寒這樣的「初生牛犢」,都不買它的帳去加入這個馬屁幫作協,而已八十多歲的金庸卻像其自著小說《天龍八部》中的人物游坦之見了阿紫姑娘一樣飛身扑進來當身作協,這怪異之舉,真如練了他小說中的癸花寶典武功一樣讓人匪夷所思,當然也就不能怪大陸許多人奉送之「老而糊塗士」稱號了!
然而,筆者以為大陸許多人是因為太不瞭解我們這位金庸金大俠的緣故,如果人們對金大俠的人生軌跡稍微瞭解一下,也就不難理解我們這位武俠巨匠的「入邪(協)了,要理解我們這位金大俠「入邪(協)的原因,其中一生與中共的恩恩怨怨,如果讓他自已執筆潑墨,不需潤色點飾,也足能夠寫一本傳奇似的小說了。
金庸,姓查,名良鏞,浙江省海寧縣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縱觀其人一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參政無門,退而候機、決裂舊巢。二、異軍突起,堪稱猛將,以文議政。三、政治情懷,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一,參政無門,退而候機、決裂舊巢
金庸在少年時期,在家鄉附近就讀,中學是著名的杭州高中學校,「杭高」是中國有數的好中學之一。中學畢業之後,適逢亂世,是日寇侵華的年代,金庸就在這時候離開了家鄉,遠走他方。據他自己的憶述,在離開了自己家鄉之後,曾在湖南省西部,住過一個時期,寄居在一個有錢同學的家中,這一段青年時期的生活,當然相當清苦。
再以後,金庸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就讀,讀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學並未畢業,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時他雖然年輕,但已才氣縱橫,覺得傳統的大學教育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報業發生關係的,是當年大公報招考記者。當年,大公報是中國最有地位的一份報紙,影響深遠,大公報在全中國範圍內招聘記者兩名,應徵者超過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之中,金庸已顯出他卓越的才華,獲得大公報錄取。
自此,金庸就進入了報界,而在不久之後,便被派去香港。金庸在香港的大公報工作了相當久,擔任的是翻譯工作。
在這個時期內,金庸對電影工作有了興趣。這種興趣的由來,大抵是由於他在報上撰寫影評之故。金庸曾用一個相當女性化的筆名寫過影評,也用「林歡」的筆名寫過影評。他所寫的影評,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尋了,但曾讀過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醒。以後,金庸直接參加了電影工作,做過導演。
金庸參加電影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其成就,和他寫作方面的成就來比較,也相去太遠,時至今日,已經很少人知道他曾實際參加過電影工作,當過編、導了。
金庸的小說創作生涯,可說開始得相當遲,他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發表,就石破天驚,震爍文壇。再接下來的「碧血劍」、「雪山飛狐」,更是採聲大作,等到「射鵰鵬英雄傳」一發表,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大宗師的地位,人人公認,風靡了無數讀者。在「射鵰英雄傳」之後,金庸因不滿大公報傾共變質,與東家發生嚴重的分歧,需要有自已的一番新天地,就脫離了大公報,和他中學時期的同學、瀋寶新先生,開始了合創明報的生涯。
二、異軍突起,堪稱猛將,以文議政
金庸脫離了大公報,和他中學時期的同學,瀋寶新先生,合創明報。明報在香港,銷量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識份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報,在國際地位上,是第一大報。連美國國務院,都會三番四次,請金庸去商議國家大事,中華民國總統,也曾數次召見金庸。
明報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提高了,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報在出版的初期,卻是一份小型報,銷數最差時,不過五六千份,工作人員不超過十人,全是憑藉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夥人瀋寶新的才幹,初創時期的工作人員如潘粵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創出了日後的天下,同時它能成為中文報紙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的其中因素之一,是不做大陸中共的應聲蟲,見解犀利、新穎而嬴得人們的青睞。
明報草創之初,金庸在明報上撰寫「神雕俠侶」,接下來,大部分小說,也全在明報上發表,一直到「鹿鼎記」。在「鹿鼎記」之後,就未曾再撰寫小說,而專注於明報的社評。
明報社評,絕大多數由金庸親自執筆,在當時它以見解之精闢,文字之生動,深入淺出,堅守原則,人人稱頌。就算意見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評寫得好,這是金庸在寫小說才能之外的另一種才華的表現。
想當初,對中共大陸當局試制原子彈,金庸的《明報》持強烈反對態度。中共黨魁陳毅針對蘇聯和赫魯曉夫對中共的制裁,撤走專家,收回核彈樣品,嘲諷中國妄想造原子彈一事,說了一句寧可不要褲子,也要核子的憤慨話。金庸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強國在於親民,現在人民窮得連飯也沒的吃,實在不該去發展核子武器。
他的言論受到中共暗中支持的香港左翼報紙的猛烈抨擊,《明報》便與《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展開了一系列筆戰。此為金庸與左翼陣營「決裂」之始。強國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那時金庸的這一思想無疑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治國理念。《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
由金庸執筆的明報社評,其影響已可與當年的大公報相埒。由於堅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則,後來金庸還曾和大公報發生過一次極為劇烈的筆戰,這次筆戰,金庸所寫的幾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嘆為觀止,只可惜這些文字,竟未曾結集出書。
這時期的金庸,可以說完全是一個俠義肝膽、為民請命的角色,沒有一點後來「老而糊塗」的影子,這期間他還用那支生花妙筆,藉助武俠小說大量地諷喻大陸現實。
1、丁春秋、任我行、毛澤東
用武俠小說中的人物來隱喻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始於《天龍八部》。「星宿派」是在隱喻什麼組織,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大陸正窮凶極惡奴役百姓的共產黨,「千秋萬載」的丁春秋老怪與「偉大領袖毛澤東萬歲」互相輝映,明白了之後,讀者一定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同樣性質的隱喻,在《笑傲江湖》任我行身上又出現了一次。
《笑傲江湖》中寫了極權令人腐化的過程。任我行對屬下本來是兄弟相稱的,可是在聽到了「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之後,在得到了教眾的拜見之後,想要阻止,一轉念間,覺得高高在上,也沒有什麼不好。先是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繼而覺得簡直好得很,再繼而覺得非這樣不可,這就給現實版的毛澤東作了註腳------權力使人腐化的過程。如果當時金庸回大陸參政成功,身處政治漩渦,老舍的跳水自盡,他非羨慕死不可,因為毛老怪一定會專門為他製造出一種政治奪命三屍腦神丸來讓他吞下不可,從而讓他住手不再寫,這絕不是什麼假設,最起碼牛棚豬窩是看好讓他住定了。
任我行最後在仙人掌峰的頂上,直摔了下來,自此與世長辭,象徵了一個在權力頂峰的人摔下來之後的下場,很有諷世意味。所以,如果將這些小說創作的年代,和當時在中國大陸上發生的事結合起來看,更加有趣,《鹿鼎記》中「神龍教」是「星宿派」的進一步,是「朝陽神教」的進一步。影子是中國大陸當時的政局,隱喻文學到這一地步,已是登峰造極。
2、教主夫人與毛皇后江青
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到「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納新」。此後又多次提及。1968年10月《紅旗》第四期社論引毛澤東進一步闡發的話:「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10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隨後,全國開始了以「吐故納新」為方針的整黨運動。(《毛澤東大辭典》第1233、844、1238頁,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只是除了正在過教主癮的毛澤東之外,當時人們弄不清楚誰是新血液,誰是廢料!
《明報》、《明報月刊》以報導、分析中共形勢而著稱,金庸自然對此倍加關注,時評政論之外,竟也落墨於不期而然之間。就在《紅旗》社論發表和轉載期間舉行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當作廢料被吐故納新,開除出黨了。半年後「九大」召開,林彪、江青的親信大量進入中共中央。
1970年初,金庸在一篇考據文字中提到「長生術」,不失時機地又指向毛老怪:「毛澤東最近屢次提到‘吐故納新’四字……」(《俠客行》第733頁),小說與大陸時局竟又驚人地同步起來,同時大陸局變也給金庸的創作提供了靈感,1969年10月23日開始寫起的《鹿鼎記》中,神龍教教徒為糊弄教主而偽造的天書中就有一句「吐故納新」。接下來的場面就更具歷史內涵了:教主在夫人的操縱下大力發展少年教眾,迫害黑龍使等老一輩教眾。「黑龍使嘆了口氣,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吐故納新,我們老人,原該死了。’」(第729、744頁)這句話,正是那時期在中共內部權鬥時,敗下陣來後一個個又被宰掉的中共黨徒們的心聲,而教主夫人與少年教眾,從頭到腳都閃爍著江青和紅衛兵們的影子。
金庸曾說:「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笑傲江湖》後記)但如果影射的內容拆射了人性呢?「吐故納新」就是這樣人性地記錄了歷史,稍一深究,歷史的真實便迎面扑來,讓你禁不住往現實中看齊。
三、政治情懷,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不能忘情於政治,是金庸貫穿一生的信念,1950年中共佔領大陸之初金庸曾赴京求職,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這次求職的失敗,意味著他當時直接參與政治的破滅,回港後,痛定思痛,才把一腔熱忱傾注於即將開始的武俠創作中,福耶禍耶?也幸虧如此,才成就了十年後他在武俠小說的創作地位,晚做了幾十年的政治奴才。
其後,金庸的政治情懷就迸發在社評與小說之間。他以文人論政的姿態接續了舊《大公報》的傳統,體現其立場的,是《明報》及其社評。社評的影響是在政治範圍之內的,由於所處環境使然,他思想裡那部分民本思想便凸顯出來。他的小說大多是反映了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對政治異化人性的厭惡、對政治人物的批判、對政治現實的失望。他甚至明確地將《笑傲江湖》標為「刻畫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頁),註明《鹿鼎記》構思與「文革」、文字獄的密切關係(《鹿鼎記》第42頁,寶文堂書店1990年版)。陳平原先生曾將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載《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是真正瞭解和讀懂金庸的知人之評。
在金庸的世界裡,小說與社評以時政為橋樑,形成了互動的關係。一方面社評的寫作給小說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進一步加深了對政治、人性的認識;一方面小說成為社評之外金庸的另一個傾訴空間。在特定的條件下,二者又與金庸個人的處境糾纏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評中抨擊極左人士,觸怒了暗中操縱左糞們的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揚言買通香港黑社會準備對金庸實施暗殺,這時候生命受到威脅的金庸沒有畏懼,他引以為榜樣的,即是自己小說中的英雄人物。
然而,曾幾何時,英雄不再往昔,隨著歲月的流失,金庸人生中的棱角被消磨殆盡,連他在小說中描寫的那些金盆洗手的江湖人物甚至都超過了他自已!晚年的金庸,政治對他的誘惑力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失而削減,終於有機會直接參於政治了。1981年夏,金庸應邀到了北京,與鄧小平長談。在香港人的眼裡,這是他對「左翼」的「回歸」開始。
他奔走於臺灣和內地之間,殷殷於國事,參加香港基本法草委會,以及後來的香港特區預委會,在這場關乎港人切身利益大是大非的「激進」與「保守」爭論中,保守的金庸屢被指為政治投機,出賣港人利益而飽受炮轟。然而金庸似乎不在乎這些,他的保守言論不由自主讓人想起了一句話:「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他的參政熱情之高,以至別人驚詫之餘還以為他仍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圖謀香港首任行政長官一職呢!如果說這些我們還彼能理解,可以在他的政治情懷中找到答案的話。而人們不敢恭維他的,是往後他與當年痛視的政府穿連襠褲的表現!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懷,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線,也就知道了金庸把自己用繩子拴在中共這條船上的「苦衷」,雖然這「苦衷」沒有幾分道理。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後,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是把緊箍在人們脖子上的繩套鬆了一個扣,似乎對知識份子開始採取了某種懷柔政策(雖然現在已證明完全是假象),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共投金庸所好所拋的繡球,竟然博得金庸春心大動,究其根源依舊是政治情懷在作祟?還是英氣消磨盡換了狗熊脾氣?還是腦子裡揉進了某種圓滑漿糊?或者幾者兼而有之吧!總之,金庸雖然感到「廉彼老矣」,已不能再擠身大陸與香港政局,但仍化裝登了場,選一個叫中共為親媽的作協來當作舞臺過了一把自已的某種夢想癮,可嘆的是雖然了卻了自己的某種心願,但也極有可能在他最後的人生中塗墨了自己的人格,給人一種畫蛇添足的滑稽感!
金庸曾表示「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金庸亦曾表示,有意寫一部「與從前的歷史觀完全不同」的中國通史,「立場完全站在老百姓一邊」,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過」作為評價那個時代的準繩。(《人民日報(華東版)》1999年4月7日)但隨著金庸的「入邪(協)」,給自己戴上了籠頭,加入了犬儒行列舍棄了意志和尊嚴,恐怕這種許諾再也不會實現了!
後記:
也有人聲稱通過研究金庸所有作品之後得出一個結論,金庸即是一個曉大義,急民生的通達人物,實質上也是一個「正邪」不分的混合體,幾年前曾有網友在「聚賢莊中的酒杯」一文中寫道:在《神雕俠侶》與《笑傲江湖》之間,金庸創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義的「正邪」的人物。楊過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顧民族大義,投到蒙古南征軍中效力,還圖謀刺殺「俠之大者」郭靖,已很難以一般意義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則以令狐沖、劉正風、岳不群等人為代表,更猛烈地衝擊了一般意義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間,還有在正邪間「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張無忌,遭受命運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無路的蕭峰等形象。那麼,金庸為什麼會對「正邪」這一主題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為什麼會一再重現這個主題?
將這幾部小說創作的時間段內金庸的經歷對照來看,就會發現它們處在一種彼此呼應的狀態之中。金庸因不滿於左翼陣營內部教條主義的束縛而自立門戶,創辦《明報》,《神雕》就開始連載於《明報》創刊之日;《倚天》開始寫作不久,《明報》經歷1962年逃亡潮報導事件,與左翼陣營顯示了差異;《天龍八部》寫作期間,《明報》又經歷了1964年因核爆問題與左翼報紙的筆戰,完全走到了舊日陣營的對立面;《笑傲江湖》寫於「文革」之初,《明報》已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反對中共「文革」的立場。這個過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極其重要的心路歷程。他是以個人的經歷為切入點,與時代背景融合在一起,堅持獨立思考,將所思所感自然流露在小說創作之中。他在描寫個人心理時,無所歸依的邊緣感、孤臣孽子的悲愴感、天地一人的孤獨感,都是相當逼真、深刻的,因為這都是作者親身的感受。他在寫這些人物、這些情感的同時,也寄託了欲說還休的潛在期望:有解釋,有呼喚,有自勉……尚在左翼陣營的梁羽生作為一位深知內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1966年寫的《金庸梁羽生合論》(載《金庸茶館》第五冊第202-232頁)中不僅敏銳地覺察到了金庸小說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轉變,還特地談到《天龍八部》裡蕭峰在聚賢莊與往日兄弟乾杯斷義、展開生死搏殺一節,並站在當時的立場上說:「讀者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作者是否要借聚賢莊中的酒杯,以澆自己胸中的塊壘?’」
這心中的塊壘是什麼?有人解釋今日金庸的「入邪(協)」已澆釋了自己胸中的塊壘,是否是這樣只有金庸自已知道了。但有一點我們肯定,今日的金庸再也寫不出當年那些神采激昂的文字了,他與佔據大陸的中共幾十年的恩恩怨怨,也隨著互相伸出彎曲的小指頭拉勾一笑,而劃上了一個使人嘆息的句號!
http://bbs.secretchina.com/viewtopic.php?f=31&t=7938
- 關鍵字搜索:
- 【長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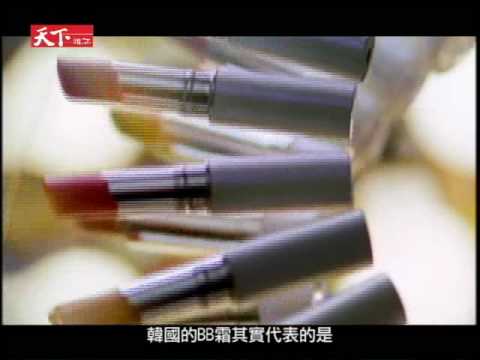







排序